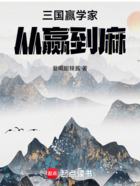
第6章 我们的有志之士实在太多了
刘慈又挨了两棍,欢欢喜喜甚至有点意犹未尽地告辞,他跟黄庸勾肩搭背地走到门口,又立刻变脸,愤怒地把黄庸甩开,恶狠狠地破口大骂,发誓不把黄庸送进去他就不姓刘!
刘慈拂袖而去,那六亲不认的步伐让周围不少人家看得胆战心惊,都替黄家捏了把汗。
哎。
黄权不愧快士之名,还真动手打人。
解气是解气,可你一个降将本来就应该夹着尾巴做人,现在居然还敢动手打人?
你看以后人家怎么折磨你家里人就完事了。
别说这些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亲手给了刘慈三棒子的黄权到现在也没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第一棒子的时候他很有报仇的快乐,可之后又是久久的迷茫,现在,这位曾经的汉军镇北将军一脸迷茫地看着朝夕相处二十多年的大儿子,似乎一下子不认识他了。
从正午到日暮,父子二人就这样对坐不语,直到天色完全暗下来,小妾在外面胆怯地呼唤黄权去吃饭,黄权这才疲惫地站起身来。
“走吧。”
“嗯。”黄庸乖巧地点了点头,又微笑着问,“父亲不问孩儿些什么?”
“没什么好问的。你也不是小儿郎,自己的事情……就自己做吧。”
黄权的口气极其冰冷,但眼神中已经抑制不住流露出了一点欣赏和宽慰之色。
作为刘备身边与法正并列的顶级智谋之士,他一直就知道儿子不甘心被软禁的平庸生活,可父子二人身在敌国都城,身边还一直有校事仔细监视,在不损害尊严的情况下能保住性命已经相当不错,黄权自己都想不出还有什么反击的手段,儿子这几年耐心在太学厮混,好像也已经甘心忍耐。
没想到就在黄初七年的元日,儿子轻轻出手,立刻就把监视黄家多年的刘慈按住,让刘慈在自己面前负荆请罪,挨了一棍子之后还要主动申请再挨两下。
这份设计巧妙,这份隐忍更让人拍案叫绝,既然儿子之前的设计没有请他帮忙,现在他自然也不会多多询问干扰,只是……
黄权终究还是好奇,走了几步,他颇为无奈地停下脚步,叹道:
“之后要作甚,提前说一声,也好让我有些准备。”
今天的事情着实把黄权给吓到了。
来到洛阳之后,儿子是他唯一的亲人,得罪刘慈的事情儿子谋划了这么久,他却完全不知情,让黄权对儿子的任性妄为有点害怕。
黄庸亦步亦趋地跟在便宜老爹的身后,看着老爹傲娇的样子,强忍着笑意道:
“孩儿知晓,日后诸事自然提前说与父亲知晓。”
黄权听儿子说是“说与父亲知晓”而不是“与父亲商量”,当即明白儿子后面的局肯定也设好,他忍不住捏了把汗,声音略带几分颤抖:
“你又要做什么?”
黄庸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今日是元日,本该去给博士、同学拜年,被刘慈这一折腾,倒是耽搁了不少时日,也只能过几日再去了。”
黄权翻了个白眼,无奈地道:
“太学才是耽搁光阴,我早就想与你说起,莫要与那些孺子胡闹了。”
曹魏太学是黄初五年(224年)才开的,这是什么概念呢——早在建安六年(201年),刘表自己就弄了一个襄阳官学、杜畿建安十一年在河东也弄了个学宫,甚至汉献帝在逃难的路上稍稍安定下来都用自己身边人凑数弄了个太学。
太学就是文脉,是一个正统王朝的象征。
可统一北方多年的曹魏直到黄初五年才搞了这个东西,不得不说实在是有点抽象了,甚至曹魏刚开国那阵子贾诩和王朗还在商量要不要干脆把经试完全取消,反正我们有九品官人法,在选拔人才上遥遥领先——这把久经考验的华歆华司徒气的暴跳如雷,撸起袖子找曹丕吵了一架这才作罢。
别看太学搞得晚,老师的队伍依旧一塌糊涂,唯一一个能通晓五经的只有河东学宫出身的乐详,其他博士大多数是来挂职混饭的。
博士这么混,来上学的弟子又不是傻子,我们自家就能学,邻家甚至还有正版的圣人经义,为啥要来这种地方消磨时间?
所以,曹魏太学名声已经完全臭了,世族子弟看不上,寒门子弟去了也都是为了逃徭役。
唯一还能坚持在太学上学的世族子弟只有黄庸自己。
黄庸去那上学也不认真学习圣人的学问,倒是凭借一双铁拳把同学都揍了个遍——哦,这倒不是因为黄庸多能打,只是因为太学其他的学生都十五六岁。
黄庸二十二岁,还在军中混过,父亲还是镇南将军,那些十五六岁的孺子那是黄庸的对手,各个被打的俯首帖耳,纷纷认黄庸当大哥。
黄权一直想让儿子别去混了。
好歹黄家也是蜀中的名门世家,来了洛阳之后开始做市井的混混,这说出去可太丢人了。
可今天的事情之后,黄权下意识地感觉到儿子有点与众不同了,他倒是没有太过阻挠,只是疲惫的目光始终盯在儿子的脸上,想要听听儿子到底有什么部署。
黄庸也需要这个便宜老爹给自己一点帮助,随即正色道:
“太学也是个好地方,只是因为大魏推行九品官人法这才让太学荒废,我等在太学与博士每谈及此事无不愤慨,每每一起商谈,约定有福同享,一起共扶汉室,呸,魏室,这些人未必就不是勠力同心的热血志士。”
热血志士?
太学有啥热血志士?
还……共扶魏室吗?
黄权听着儿子的话,不禁哑然失笑,思绪又飘回了多年前的午夜。
那夜汉中的细雨如纱,汉军军营觥筹交错,杯盘狼藉,众将相互枕藉,呼吸都是浓郁的酒香。
法正靠着黄忠,黄忠倚着魏延,魏延吐了一地,兀自满脸幸福地冲着赵云喃喃自语询问这一战他比当年赵云在长坂坡如何。
而赵云微笑着轻轻擦拭长剑,与黄权对坐闲聊,两个人对坐看着细雨初晴的夏夜里漫天明亮的星斗,当年银枪白马的赵云老气横秋地长叹着,说自己老了,想念家乡,想念常山的大雪中陪他一起练武的姑娘。
黄权当时并没有多少乡愁,他看着这个身经百战的老将,微笑着说过几年做成大事,昂首回到北方,当年的姑娘不在,他们群臣也能一起赏雪。
可现在……
现在他真的来了北方,当年不曾见过的大雪也已经看厌,可身边的人啊,却只剩下他和儿子了。
儿子胸怀大志,身边总需要一些人物帮助,就是……太学那些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真的有用吗?
身为人父,黄权非常希望儿子能托庇在一棵大树之下,而不是在他乡靠自己一人在漩涡中搏斗,当年他们在汉中时众星云集,最后在夷陵还不是功败垂成,儿子并无什么依仗,陈蕃、李膺那样发动诸生最后还是功败垂成,更何况现在太学博士也都是一群虫豸,有个屁用。
黄权直勾勾地看着儿子,略带几分担忧地道:
“太学之事,素来牵扯重大,若无人依仗,万不可轻举妄动。”
这是一个长者的人生经验,尽管黄权觉得儿子很聪明,但还是要提醒儿子一下。
可黄庸闻言只是轻轻点了点头,随即正色挺起胸膛。
“有的!父亲,有的!要是没有靠山,太学之事,我岂能轻易妄为,又如何能说服刘慈?”
“啊?”黄权一时摸不到头脑,没想到儿子居然还真的有靠山。
这下他更担心了。
他们这种降将能有什么靠山,这怕是有人利用儿子年轻气盛,想要趁着曹丕病重做点事情,怪不得刘慈前倨后恭,这怕是……
哎,年轻人不知深浅啊。
黄权渐渐严肃起来,心道便是拼了老命不要,沉声道:
“是何人如此大胆?”
黄庸微微一笑,念出了一个让黄权差点魂飞魄散的答案:
“是孩儿的好兄弟,骠骑将军……曹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