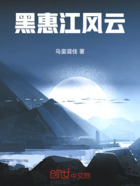
第13章 阿婆口中的珠街解放(上)
一、火塘红
昌宁县珠街的夜,是被山雾和松涛泡软的。七月的尾巴,暑气尚未完全退去,但深山里的风已经带上了一丝凉沁。乌蛮滋佳的阿婆坐在自家木楞房的火塘边,手里握着一段刚劈好的栗木柴,正往跳动的火焰里送。
火塘是这栋老房子的心脏。青黑色的塘泥被几十年的烟火熏得油亮,塘边嵌着的三块三角石稳稳当当,支起一口黑黢黢的铜锅,里面煮着的苦荞茶散发出浓郁的、带着点涩味的香气。阿婆脸上的皱纹很深,像火塘边被岁月刻蚀的岩石,可那双眼睛,在火光的映照下,却亮得惊人,仿佛藏着整个珠街的日出月落。
“阿婆,火塘边烤的苞谷是不是熟了?”说话的是阿婆的外孙乌蛮滋佳,他凑到火塘上烤得金黄的苞谷,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阿婆“嗬嗬”地笑起来,用粗糙的手指弹了弹乌蛮滋佳的额头:“小馋猫,就知道吃。等你阿公从牛圈回来,一起吃。先坐好,阿婆给你讲古本(故事)。”
乌蛮滋佳准立刻乖乖地盘腿坐下,挨着阿婆暖烘烘的膝盖。火塘的另一边,阿婆的女儿乌蛮滋佳的姨妈段阿秀,乌蛮滋佳的阿妈段阿英正在收拾碗筷,听到“讲古本”,也忍不住侧过了耳朵。
木柴在火塘里发出“噼啪”的轻响,火星子溅起来,又倏地熄灭在半空。阿婆往火塘里添了些火灰,让火焰更柔和些,然后慢悠悠地开口,声音像是被火塘煨过,带着一种独特的沙哑和温暖。
“你们啊,现在日子好过了,穿得暖,吃得饱,还能去乡里的学校念书。可阿婆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那日子啊……”她顿了顿,目光透过跳动的火苗,望向木楞房外浓得化不开的夜色,仿佛穿越了漫长的时光,回到了那些被汗水和泪水浸透的岁月。
“那时候,三条河从这里交汇,彝家人叫它岔河。我家住在上山叫苦荞坪,为啥叫苦荞坪?因为地里种不出多少粮食,一年到头,除了苦荞还是苦荞,吃进肚里都是苦的。”
阿婆的声音低沉下来,火光照在她沟壑纵横的脸上,明明灭灭。
二、苦荞坪的泪
“阿婆我啊,本名叫阿果莫,就是‘小果果’的意思。生在苦荞坪最穷的一家,阿爸给地主家扛长工,阿妈就给富人家的婆娘做针线,换点吃的。那时候的主人,姓杨,住在山梁上那座青砖大瓦房里,对我们彝家人,那是连正眼都不瞧的。”
阿婆的手无意识地摩挲着膝盖上打了补丁的围裙,那布料磨得光滑,是她年轻时用土布织的。
“我七八岁的时候,就跟着阿妈去富人家干活了。天不亮就得起来,背水、劈柴、喂猪,富人家的婆娘拿着鸡毛掸子,动不动就骂‘蛮子’、‘贱骨头’。有一次,我不小心打碎了她一个装胭脂的小瓷瓶,她拿起鸡毛掸子就往我身上抽,打得我胳膊上都是红印子。阿妈跪在地上求她,她才骂骂咧咧地住手,还扣了阿妈半个月的口粮。”
乌蛮滋估听得眉头紧锁,小手攥成了拳头:“那个富人婆真坏!”
“坏的不止她一个。”阿婆叹了口气,“那时候,彝家的女人啊,命比苦荞根还苦。从小就要干活,长大了,就被父母嫁给不认识的男人,换几担谷子、几匹布。嫁过去,就是伺候公婆、男人,生娃带娃,一辈子困在锅台和地里,连自己的名字都快忘了。”
她顿了顿,眼神里掠过一丝痛楚:“阿婆我十六岁那年,阿爸阿妈就把我许给了山那边一个姓罗的人家,说是他家有几亩薄田。我连那男人长什么样都没见过,就被一顶破轿子抬过去了。那男人是个赌鬼,喝了酒就打我,家里的活全丢给我一个人。天不亮就去背水,要背够三缸,才能吃一口稀得能照见人影的包谷糊糊。白天要下地干活,割草、砍柴、种包谷,晚上回来还要纺线织布,给公婆和男人做衣裳。”
火塘里的火又旺了些,映得阿婆的眼睛里似乎有泪光在闪。
“有一次,我怀孕了,挺着大肚子还得去背柴。走到半山腰,脚一滑,就滚了下去。还好被几棵小树挡住了,可孩子……没保住。”阿婆的声音哽咽了,“我躺在地上哭啊,哭我的孩子,也哭我这苦命。可我男人知道了,不仅没安慰我,还骂我没用,连个娃都保不住,回来又是一顿打。”
乌蛮滋佳的阿妈听得眼圈红了,轻轻拍了拍阿婆的背。旁边听的乌蛮滋佳的三姐似懂非懂,只是觉得心里闷闷的。
“那时候的彝家女人,就像地里的野草,风吹雨打,没人疼,没人管。”阿婆深吸了一口气,像是要把那些沉重的往事都吐出来,“我们不敢反抗,也不知道怎么反抗。只觉得这辈子,就该是这样的命。直到有一天,山外面来了一群人,穿着黄布衣服,胸前戴着牌牌……”
三、山外来的“菩萨兵”
阿婆的语气渐渐变得明朗起来,眼神也跟着亮了。
“那是一九五〇年的春天,苦荞坪的迎春花开得满山都是。有一天,寨子里的狗叫得特别凶,大家都吓得躲在屋里,以为又是国民党的败兵来抢东西了。可等了半天,没听到枪响,只听到有人在外面说话,声音温和得很。”
“我壮着胆子,从门缝里往外看,只见一群人背着枪,穿着整齐的灰衣服,排着队站在寨口的大黑树下,没进一家门。领头的是个年轻的汉子,脸上带着笑,跟寨子里最有威望的毕摩(彝族祭司)说话。后来才知道,他们是解放军,是毛主席派来的‘菩萨兵’,是来帮我们穷人翻身的。”
“解放军来了之后,就在寨子里住下了,跟我们同吃同住。他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帮着我们挑水、劈柴、种地。那个领头的李连长,还会说几句简单的彝话,见了老人就叫‘阿波’(爷爷)、‘阿婆’,见了年轻人就叫‘阿弟’、‘阿妹’。我们从来没被这么尊重过,心里头暖烘烘的。”
阿婆的脸上露出了笑容,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带着感激的笑。
“李连长他们来了之后,就挨家挨户地访贫问苦,跟我们说‘天下穷人是一家’,说‘地主老财的剥削是不合理的’,说‘我们彝家人也要当家做主’。刚开始,我们都不敢信,觉得这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可他们天天讲,还带着我们斗地主,把地主家的粮仓打开,把粮食分给我们穷人。”
“记得分粮食那天,好多人都哭了。我也哭了,不是因为难过,是因为高兴,因为从来没想过,我们也能有自己的粮食。李连长还跟我们说,女人和男人一样,都是平等的,女人也可以参加工作,也可以学习文化。”
乌蛮滋佳好奇地问:“阿婆,那你参加了吗?”
“参加了!咋能不参加!”阿婆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解放军来了之后,就组织我们成立了妇女会,我第一个报了名。李连长的爱人,张同志,是个女解放军,她教我们唱歌,教我们认字,还教我们怎么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张同志跟我们说:‘姐妹们,我们彝家女人不是男人的附属品,不是地主老财的奴才,我们是新社会的主人!我们要站起来,反对封建压迫,反对包办婚姻,我们要自己说了算!’”
阿婆的手在空中有力地挥了一下,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激情的年代。
“那时候,我就像变了个人似的。以前连大声说话都不敢,现在敢在妇女会的会上发言了,敢跟那些还在欺负女人的男人讲道理了。有一次,我们寨子里有个男人又打老婆,被我们妇女会知道了,我们几十号人跑到他家去,把他围起来,你一句我一句地批评他,吓得他再也不敢打了。”
火塘里的茶开了,“咕嘟咕嘟”地响着,阿婆伸手把铜锅往旁边挪了挪,热气氤氲了她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