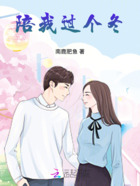
第1章 外婆
外婆祭日那天,我和大姨的女儿小林一起坐在院子一角晒太阳——人就是这样,不管你几岁,只要父母还在场,就只有“大人说话,小孩子一边玩儿去吧”的份儿。表弟和大舅二舅在里头忙忙活活的,小林把瓜子壳丢在地上,说,哥,其实外婆以前跟你最亲近——她老给你塞零花钱吧,过年的时候你不回来我们都没得红豆沙吃。我的脑子“扑腾”了半天,很想能有点什么事来证明我和外婆的确十分亲近——很可惜没有,关于她的记忆好像只有那场初冬的葬礼。那会儿我在上海参加播音专业的艺考集训,老师拿着电话从后门走进来,不轻不重地按了一下我的肩膀。我站在走廊里控制着自己不住发抖的身体,不断说着“好”,甚至没有来得及回宿舍拿一件御寒的衣服,就开始了我的千里奔丧之路。刚去集训的时候我走过一次反方向的,满心都是对未来的憧憬——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家和上海之间的距离那么遥远,远得他们只来得及通知我回去磕头。到家时已是凌晨,到外婆家院门口得要经过一条巷子。斑斑驳驳的黄泥从巷子两边的墙面上掉下来,挂在我的风衣外摆上——那件在上海被同学夸过许多次、没有什么御寒功效的衣服被粗糙的墙面挂出几个小洞。这条巷子两头透风,就像我的脊柱——初冬的风穿过这条巷子,就像一场雨从我脊柱的这头浇到那头,痛得彻骨。我爸拎着我的包沉默地打开门,院子里站着、坐着许多披麻戴孝的人,面容在黑夜里有些模糊。他们看着我,瑟瑟低语着。应该是在说,可算赶回来了,虽然外孙回来也就是磕个头。遗照和棺木摆在正屋。外婆是个很活泼的小老太太,我一下就看出遗照是我拍的——她笑得很灿烂。我妈跪在那个被油刷得透亮的棺木前面,撑着一双红肿的眼烧纸。我上去跪在她边上,她拽住我的手腕,在我跳动的脉搏上轻轻地摩挲了几下。“来,看看外婆。”我探身往棺木里看了一眼,母亲给她穿上了她最喜欢的那件袄子——我甚至能记得这件袄子上的味道,沾着一点红豆沙的甜,还有一点阳光的味道。儿时外婆常穿着这件袄子抱我,或者给我煮一碗甜甜的红豆沙。而后我低下了头,母亲把我揽进怀里。有什么温热的东西顺着我的脖颈滚进脊柱深处。妈妈,是不是雪落了。葬礼上总有一个万分理智的人,你从他的面目中见不到悲伤。他走过来拍拍我妈的肩,妈妈会意,拉着我站起来。第一站是殡仪馆,队伍已在院子里按顺序排好。表弟抱着照片往人前一站,唢呐声便响起来——夹着鸡啼,像要刺破夜空。人们开始忙碌起来,叮叮当当地把棺木钉起来。我撑着眼望着前面,不知道过了多久——应该很久,久到表弟烦躁地跺了跺脚,怀里的“外婆”也跟着颤了一下。前面人示意了舅舅一下,舅舅和表弟先跪下了;我本也想一起,妈妈拉住我,哑哑地说了句“等一下”。等舅舅们站起来,司仪喊了一声女儿外孙什么的,我妈就跪下了,我也跟着跪下。磕头,磕头,再磕头。我的前额落在粗糙的水泥地上,起来时沾了点薄灰,这就是再见了。棺木送上车,舅舅一家坐在那辆车上,我爸开着车带我们跟在后面。我们要顺着嶙峋的夜路开到更郊外的地方。初冬天亮得晚,我难得见到这种透着点暗色的蓝,那是用语言很难形容的感觉——我忽然就明白为什么蓝色用来形容忧郁。车灯破开荡着薄雾的前路,像扫清去往下一辈子的障碍,也像一块泡腾片丢进凉水里那样,酸涩得发胀。等到沉沉往事都变成一捧土,外头又淅淅沥沥落起雨了。那么长的一段人生,最后也只变成一个小瓷坛子。我们又坐上车,母亲说外婆在好多年前外公走了的时候就和风水师一起给自己选了地方,离外公的不远,面朝着一条河。我看着他们将那个小坛子放进墓里,然后把外婆的手机、手镯、耳环什么的一一摆进去。我妈戳了戳我,说,来,这个你自己放进去。是我小时候的照片。我把它摆在外婆的手机边上,我记得我到外地上学之后隔很久才能回家一次,外婆就捏着这张照片和我打电话。她说,哎呀,以前才这么大点,现在都这么帅了。什么时候来呀,外婆想你了……外婆,你到了那头,也给我打电话吧,梦里的那种。这下换我想你了,外婆。片刻之后,人群缓缓朝坟坑移动。大舅和二舅手中提着不同的袋子,按照老家习俗,要向坟坑洒酒驱虫,抛洒中药材及五谷杂粮。我和爸妈静静地站在一旁看。我突然想到,刚刚磕头的时候,孙子先跪下,外孙才能跪下。其实我很想去捧那张照片——我是外婆带大的,但表弟是在城里长大的,我总觉得我要比表弟跟外婆更亲一些。但他是儿子的儿子,我是女儿的儿子。表弟拎着一袋红豆撒,他来来回回地走,古人说红豆最相思,能不能让我也撒一把,我试探着要伸出手去,我妈看了我一眼,拍了一下我的手背,“不可以的,外姓人不能做”。“哥,给奶奶撒点红豆。”表弟看着我妈,掏出一小把红豆塞到我手里,嘴里嘟囔着,“什么内孙外孙,不都是孙。”我看着那把红豆,它们从我的掌间“噼里啪啦”掉下来,落在瓷罐子上,听起来很热闹——人啊,在一片热闹里来,在一片热闹里去。
灵车拐过最后一道河湾时,天光终于刺破云层。我望着车窗外波光粼粼的河水,突然想起外婆总说这条河是活的,冬天会缩成银色的细线,春天又会涨成翡翠腰带。
老宅院里的白幡在晨风里卷成漩涡。大舅二舅蹲在檐下抽烟,火星明灭间,我听见大姨在厨房喊:“红豆沙熬好了,都来喝碗热的。“人群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三三两两往厨房飘。
我站在堂屋门口,看着供桌上外婆的瓷罐。晨光斜斜切进来,那捧红豆在瓷罐口闪着玛瑙般的光。表弟不知何时站到我身后,手里端着两个青瓷碗,“哥,尝尝?“红豆沙在碗里凝成琥珀色的镜面,倒映出我们相似的眉眼。
厨房灶台的火塘还温着,我舀了半勺送进嘴里,舌尖突然被记忆刺穿——十岁那年出水痘,外婆用棉被把我裹成蚕蛹,一勺勺吹凉红豆沙喂我。那时她袄子上沾着的,就是这个味道。
“小林说外婆往年都存着陈年红豆。“表弟用筷子在碗底画圈,“就埋在厨房地窖的陶瓮里,说要等你过年回来......“他的声音突然卡在喉咙里,碗沿磕在灶台上发出清脆的响。
我举着煤油灯钻进地窖时,霉味混着土腥气扑面而来。角落的陶瓮盖着青布,掀开时簌簌落下一层灰。暗红色豆粒间躺着个铁皮盒,生锈的锁扣轻轻一掰就开了。
盒子里是整整齐齐的糖纸,每张都压得平平整整。荔枝味的、橘子味的、花生牛轧的,都是我小时候攒了送给外婆的。最底下压着张泛黄的纸,铅笔字歪歪扭扭写着:“给外婆买新袄子——明明,七岁。“
地窖的土墙突然变得潮湿。我数了数糖纸,正好是我离开老家去城里读书的年数。原来每次寒暑假回来,茶几上突然出现的那些消失多年的水果糖,从来都不是巧合。
回到院子时,表弟正在扫银杏叶。金黄的扇形叶片堆成小山,他忽然说:“去年秋天奶奶拉着我拍短视频,说要发给在上海的明明哥看。“手机屏幕亮起,视频里外婆举着自拍杆转圈,老棉鞋踢起漫天银杏雨,“小明你看,外婆这件袄子还是你妈买的......“
北风卷着最后几片叶子掠过屋檐。我摸到口袋里那颗偷偷藏起来的红豆,坚硬的表皮在掌心硌出月牙形的痕。厨房飘来新熬红豆沙的香气,混着线香未散的余韵,在冬日稀薄的阳光里织成温暖的茧。
表弟把扫帚靠墙放下,忽然从裤兜掏出一串钥匙:“奶奶房间的樟木箱最底层,有件东西该给你。“铜钥匙在锁孔里转动的声响,像极了小时候偷吃冰糖罐时的心跳。
樟木箱开启的瞬间,陈年的艾草香裹着水汽涌出来。墨绿绸布下压着件叠得方正的靛青袄子,正是外婆葬礼时穿的那件。表弟的手指抚过领口磨白的缎边,“奶奶说这是你妈工作后买给她的第一件衣裳。“
袄子底下躺着本缎面册子,翻开却是两面截然不同的家谱。左侧是工整的毛笔字记载的族谱,右侧用铅笔歪歪扭扭添了许多名字——我的名字紧挨着表弟,墨迹还新得发亮。
“去年清明奶奶让我写的。“表弟的指尖停在我的名字上,“她说祠堂里的木头牌位太冷,要在这里给外孙也留个暖和地方。“
夜色漫进来时,老宅突然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西北角的厨房在积雪重压下轰然倒塌,椽木折断的声响惊起满院寒鸦。我抓着铁锹往废墟里挖,指甲缝里嵌满冰雪与木屑,直到触到那个冰凉的陶瓮。
破碎的瓮身露出层层叠叠的红布包,每包都系着月份牌裁的纸笺。最早那包写着“小明去省城读书“,最新那包墨迹尚润:“小明当上主持人“。红豆从豁口倾泻而出,在雪地里滚成血珠似的轨迹。
守灵最后一夜,我抱着暖水袋蜷在外婆常坐的藤椅上。表弟忽然推门进来,军大衣裹着怀里的陶罐直冒热气:“我用塌了的灶砖搭了个临时灶,熬了最后一锅红豆沙。“
瓷勺碰着碗沿叮咚作响,表弟从罐底捞出个铝箔包。剥开七层油纸,竟是块凝结着冰碴的绿豆糕——那是我艺考前夜,外婆托顺风车捎到上海的,当时嫌累赘塞进了行李箱深处。
“那天奶奶盯着物流信息刷到半夜。“表弟把糕点泡进红豆汤,“说绿豆降火,红豆补血,凑一起才镇得住大场面。“
雪光透过窗纸漫进来,我们在供桌旁并排躺下。表弟摸出手机播放葬礼时拍的视频,快进画面里人影幢幢如皮影戏。放到撒红豆那段,他忽然摁下暂停:“你看奶奶的瓷罐。“
放大画面,那些叮叮当当砸在青瓷上的红豆,竟在釉面弹跳成模糊的笑脸。表弟把视频调成0.5倍速,在某个瞬间,一粒红豆恰好卡在瓷罐描金的眼睛位置,仿佛外婆在朝我们顽皮地眨眼。
后半夜风雪更甚,老宅屋檐垂下三尺冰凌。我们缩在被炉里翻看外婆的手机相册,最新照片停留在她举着自拍杆站在银杏树下的样子。表弟忽然指着照片角落:“看这个反光!“
放大镜功能让模糊的光斑逐渐清晰——厨房玻璃窗上,少年时代的我正在偷吃晾晒的柿饼。原来在我不知道的时空里,外婆的镜头永远留着一块属于我的位置。
晨光初现时,大舅抱着被雪打湿的族谱来找我们。泛黄的纸页间飘落张铅笔素描,画着穿开裆裤的男孩蹲在灶台前吹火——我的后颈上有块月牙胎记,此刻正在发烫。
“你外婆跟风水师学画符时偷练的。“大舅的烟头在晨雾里明灭,“她说记性会骗人,画下来的才算数。“
送葬队伍再次集结时,我主动接过了引魂幡。表弟把装红豆的布袋剪开道小口,我们踏着积雪往坟山走,暗红的轨迹蜿蜿蜒蜒,像大地的毛细血管正在苏醒。
阴阳先生唱诵的间隙,我听见积雪压断枯枝的脆响。那声响渐渐与记忆重叠,是十二岁那年除夕,外婆教我剪窗花时,红纸在银剪下绽开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