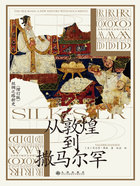
第二章 龟兹:丝路诸语之门
远在现代词典与语言教科书诞生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作为各民族的交汇之处,丝绸之路一直是语言交流的场所。佛教徒希望把原本用梵语表达的复杂深刻的佛理翻译出来传达给信众,因此他们对语言教学最为热心。坐落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龟兹是个繁荣的绿洲,它在语言方面比丝路其他地方更有优势,因为当地的龟兹语和梵语同属印欧语系①(龟兹语文书如下页所示)。龟兹自然成了佛教进入中原的门户。龟兹绿洲也让僧人有机会见到操着各种语言来到这里的旅行者,因为当时的龟兹是丝路北道最大、最繁荣的地区,只有高昌能与之匹敌。
最有名的龟兹人是鸠摩罗什。他是把梵语佛经译成通顺易懂的汉语的第一人,极大地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1]由他主持的译经团队把大约三百种佛经从梵语译成了汉语,包括著名的《妙法莲华经》。(经在梵语中指佛说的经典,实际上很多佛经是公元前400年左右佛陀去世之后很久才形成的。)尽管后来的新译者一直想改进,但鸠摩罗什的很多译本由于其可读性一直被沿用至今。

丝路通行证(过所)
图中过所长8.3厘米、宽4.4厘米,上面用婆罗米字母龟兹语写着边检官员、验收过所官员和过所持有人的名字。曾经出土的大约一百多件类似过所,一般会在后面列出随行人员和牲口,但此过所缺失这部分。过所用墨写在有凹口的杨木上,原本有盖,用麻绳绑好并加封。现存过所没有一件是完整的。(法国国家图书馆供图)
来源 BNF, Manuscrits orientaux, Pelliot Koutchéen LP I + II.
鸠摩罗什是一位非凡的语言天才,和许多龟兹人一样,他掌握了多种语言,包括母语龟兹语,以及梵语、犍陀罗语,可能还会焉耆语和粟特语。鸠摩罗什的父亲是犍陀罗人,和尼雅移民一样讲犍陀罗语。粟特语在撒马尔罕地区流行,焉耆语通行于丝路北道的焉耆(在龟兹以东约300千米)附近。焉耆的维吾尔语名称转写为喀喇沙尔(Qarashahr)。鸠摩罗什及其同僚使用婆罗米文读写龟兹语和梵语,他们可能也学过佉卢文,这种文字在公元400年左右就基本不再使用了。
本章将要讨论这些语言,还会特别强调自1892年以来各国学者为破解失传的龟兹语、焉耆语所付出的巨大心血。全世界的学者花了差不多一百年的时间研究龟兹语,不仅要破解这门语言,还要理解它与同属印欧语系的焉耆语的区别。当然这些心血在后来得到了回报。
世界闻名的克孜尔石窟在库车以西约40千米,开凿工作于鸠摩罗什在世时便已开始。该石窟是新疆最吸引人的旅游景点之一。今天,人们乘飞机、火车或汽车到达库车或库尔勒后,再转车即可到达石窟所在山谷。但在过去,至少一百年以前,几乎所有人都是坐船顺流而来的。冰川融化形成的众多河流都经过塔克拉玛干沙漠,顺着沙漠北缘流淌的塔里木河是其中最大的一条。它在库车附近有两条支流:库车河和渭干河,后者恰好在克孜尔石窟前流过。如今中国西北用水量巨大,这些河流的水量减少了很多。今天如果想坐船横跨沙漠,那必须得赶在早春水位最高的时候。而一个世纪以前,只要不上冻,这些河流几乎可以全年通航。
我们只需读读瑞典人斯文·赫定的精彩游记,便可知一百多年前的库车地区与现在大不相同。1899年秋天,赫定买了一艘约12米长、吃水不到30厘米的渡船。他在甲板上搭起了帐篷、暗房,以及一个做饭用的黏土灶。因为有人提醒过他河道在巴楚附近会变窄,他还带了一艘“不到那渡船的一半大”的小船一起航行(见彩图10)。

彩图10 斯文·赫定乘船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
如今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绝大多数河床都已彻底干涸。但在1899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乘着图中这艘12米长的船探索了这一地区的水路。他从叶尔羌(今莎车)以北出发,航行82天,里程达1500千米,最后由于河中有大块浮冰便在距库尔勒三天路程的地方结束了航程。赫定的水彩画显示他的船甲板上有帐篷、用作暗房的小木屋和做饭用的陶炉。
来源 From Central Asia and Tibet, facing p.106.
赫定的航行始于新疆西端的莎车(旧称叶尔羌,位于喀什东南不远)。他生动地描绘了1899年9月17日他从莎车莱利克(Lailik)码头启航时的情形(见史料12)。出发那天,赫定记录道:“河面宽134米,水深约2.7米。”[2]

六天之后,赫定到达叶尔羌河分为诸多支流之处,每条支流都暗藏着危险。
河床变窄。水流以惊险的速度带着我们前行。水花在我们周围翻腾,生出许多泡沫。我们顺激流而下。河道之窄、转弯之急,使我们无法控制船体。大船猛烈地撞到岸边,我的箱子差点掉下船去……水流一直如此湍急,而我们又航行得非常快,以至于船触河底时差点翻船。
激流突然停了,大船陷入淤泥之中。赫定雇了三十个人把大船拖出来之后才能继续航行。
赫定沿着叶尔羌河继续北行。叶尔羌河与从北流过来的阿克苏河汇聚成塔里木河。赫定继续向东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空闲的时候他会在小船上扬帆,让大船跟在后面。水流很急,速度达到每秒近1米,而且水中的冰块越来越大。赫定在距离库尔勒还需三天路程的新湖(Yongi-kol)中止了航行。82天的航行,他走了近1500千米。[3]如果赶上夏天,早上能早一点出发,他或许可以再航行300千米到达库车。
赫定的探险在欧洲激起人们极大的兴趣,英国、法国和德国都分别组织了考察队。德国人连续进行了三次考察。第二次考察的领队阿尔伯特·冯·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居然以扔硬币的方式决定向北去库车,并于1906年抵达克孜尔石窟。他发现了全中国最美的宗教石窟之一。339座洞窟开凿于绵延两千米长的山壁之上。[4]有些洞窟很小,有些则有11米至13米高、12米至18米深。渭干河在其南7千米处流过。石窟前的绿洲景色非常怡人,有时还能听到布谷鸟的叫声,这叫声在现代中国可是非常罕见了。
克孜尔的山崖由砾岩组成。砾岩是一种较软的岩石,很适于开凿洞窟。但这样的洞窟很容易坍塌,所以开凿者经常在洞的中央留一根柱子用于支撑。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由于地震的破坏,很多外室都坍塌了,使内室完全暴露在外。1906年3月,勒柯克和提奥多尔·巴图斯以及他们的雇工就经历了一次地震。勒柯克对此次地震的描述如下:
忽然一阵剧烈的像打雷般的巨响从我们头顶滚过。……这时灾难发生了,一切都是那么快,仅仅瞬息之间。我看见巴图斯和他带的工人们突然趴在陡峭的山坡上。我还没明白过来这是怎么一回事,我身边的雇工们也一声尖叫趴在地上,我立即跟他们一起趴了下来。就在这一瞬间,大量岩石铺天盖地朝我们砸下来,重重地落在我们身边,值得庆幸的是没有人受伤,这真是让人不可思议的特别的一天。
这时,我向着山谷河流的方向望去,只见河水剧烈地荡来荡去,拍打着堤岸。在山谷顺着河流的远方突然升起了巨大的尘土,像云,更像巨大的柱子,一直升到无际的天空。同时大地开始震动,在悬崖周围发出雷鸣般的巨响。这时我们才意识到地震了。[5]
虽然石窟有坍塌的危险且其中很多壁画都被勒柯克等人挖走,但还是有很多壁画在原址上保留了下来,今天也能看到。克孜尔周围还有其他有壁画的石窟群,其中库木吐拉石窟规模最大,最值得一去。
克孜尔的很多洞窟都有相同的结构:洞窟中心有一根柱子,信徒进洞来可以绕行一周。佛陀去世后,人们在北印度建起了佛塔以供奉佛骨,从那时起,信徒们就以右绕佛塔的方式来表达虔信。在西域,人们也绕塔礼佛。与尼雅和米兰的佛塔不同,洞窟里的中心柱中并无佛祖遗骨。柱上一般有放有佛像的佛龛,佛像现在大多已经遗失。
建于公元400年左右的克孜尔38号窟是开凿最早,也可能是最璀璨夺目的一个洞窟。[6]38窟的背墙上画的是涅槃像,佛陀侧卧于榻上,周围是来礼敬他的各国君王。站在中央柱处向洞窟出口方向看,可以在出口之上看到弥勒佛,他是掌管未来天国的佛。
沿着38窟拱顶的中轴可以看到印度的日神、月神、风神,两尊带火的立佛,以及双头的金翅鸟。这种金翅鸟是印度传说中一种护持佛法的鸟。这些神像有明显的印度风格,很有可能出自印度画师,或者基于印度样本而作。勒柯克把这些画称为“湿壁画”(fresco)。但事实上它们是绘于干石膏之上的,严格来说并不能被称作湿壁画,因为湿壁画特指绘于湿石膏之上的壁画。开凿洞窟的技术来自印度,那里有辉煌的阿旃陀石窟,就在孟买郊外,还有其他早期佛教遗迹。

克孜尔石窟结构图
很多克孜尔石窟结构相同。信徒从前室穿过一道门进入主室,绕行中心塔以示虔敬。塔中有佛像,并饰以石头和树枝来表现须弥山,即佛教观念中处于宇宙中心的山。原本盛放这些装饰品的佛龛常常依旧可见。洞窟后壁上绘着佛陀涅槃像。(美国华盛顿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供图)
来源 Courtesy of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and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38窟中轴线的两侧是一排排菱形格子,这些菱形就像邮票边上的锯齿互相嵌在一起。一排是佛譬喻故事,一排是佛本生故事,即佛陀前世的故事。譬喻故事也叫因缘故事,画面中都有一尊坐佛,旁边有一个人物。绘制这些譬喻故事的目的在于教育听众,使他们知道今世的行为对来世是有影响的。

克孜尔石窟壁画
这幅石窟窟顶壁画展现了克孜尔特有的邮票式菱格。当地画师在这些菱格中描绘佛陀前世的故事。每个菱格中画有一个佛本生故事中的主要事件,让讲故事的人以此为线索,为洞窟参观者讲解整个故事。
来源 From The Art in the Caves of Xinjiang, Cave 17, Plate 8.
佛本生故事一般都是通过重新阐释印度民间故事来讲授佛教的价值观。比如,猴王故事讲的是一群猴子偷了国王花园里的果子,国王的护卫追猴子一直追到一条大河边。猴王用自己的身体做桥让其他猴子过河,之后它自己却受伤了,直到国王被它感动将它救下(见史料14)。按照佛教的解释,这个故事表现了佛陀(即猴王)舍身为人的精神。
另一个佛本生故事在好几个洞窟里都出现过,它对商人特别有吸引力。故事是这样的:五百个商人在夜里赶路,因为天太黑了什么都看不见。他们的头领,即佛陀的前世,用白毡蘸满黄油包住自己的胳膊,之后点燃毡子高举手臂为商人们照亮前方的路。在这个故事里,佛陀又一次舍己为人。听僧人讲这些本生故事的信徒可以明白,涅槃只有佛陀和少数高僧能够做到,这是早期佛教的一条关键教理。
克孜尔最大的石窟(47窟)现在空空如也。16.8米高的石窟中本来有一尊大佛像,顺着渭干河来的旅行者应该从很远处就能看到。这种巨大的佛像窟并非起源于克孜尔。开凿克孜尔的工匠一定听说过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这座大窟左右两边各有五排孔,以前应该插有木桩支撑着一个平台,平台上面是大佛像两侧的小佛像。克孜尔其他的洞窟里也曾经有过大佛,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有一位自中原来访的僧人曾经记载,西城门外立有两尊九十余尺高的佛像,这两尊佛像在五年一度的大法会上受到礼敬。[7]
今天就算再不细心的游人也能注意到克孜尔石窟的窟壁上有很多壁画被挖走了。世界上所有重要的东亚艺术收藏机构都有来自克孜尔的壁画,画上所用的青金石蓝和孔雀石绿还鲜艳如新。绝大多数壁画都是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被挖走的,其中柏林的藏品格外丰富。
勒柯克发明了一种转移这些易碎壁画的新技术。他不无骄傲地描述道:“首先,用一把非常锋利的刀子将壁画切成弧形,要小心切透窟壁上的涂层……这之后,要用鹤嘴锄在壁画边上凿个洞,给狐尾锯留出空间。”(见史料13)[8]这种一步一步的描述读后让人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因为我们很容易想象到这种方式对艺术品的破坏。有些欧洲人坚决反对把壁画挖走。勒柯克的同事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觉得应该描绘并准确测量遗址,然后在欧洲原样复制。他的这种观点在当时属于少数派。
第三批探险队抵达一年之后,法国学者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在1907年来到库车。他在这里停留了八个月,收集了很多龟兹语的重要文书。他还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探索向北穿越天山的路线。他发现,沿着渭干河离开克孜尔向北,有两条路连接着塔里木盆地与北方草原。[9]草原包含新疆北部(准噶尔盆地),并一直延伸至今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这里是许多游牧民族的家园。许多世纪以来,这些游牧民族一直威胁着中原王朝。
由于地处通往北方草原的咽喉要道,在西域各绿洲中,龟兹最先在汉文正史里出现。公元前2世纪末,汉武帝派李广利进攻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的大宛,汉朝大军便途经龟兹。[10]和楼兰王一样,龟兹王尽可能与汉、匈奴同时交好。匈奴控制了今蒙古草原,是汉朝的敌人。公元前176年至公元前101年之间,龟兹王向匈奴称臣,并把自己的儿子送去做人质。当时的臣属国一般都会把王储送到宗主国学习文化、熟悉风俗。
公元前1世纪,匈奴式微,龟兹王转而向汉朝称臣。[11]公元前65年,龟兹王和王后双双来到汉朝国都长安,并停留一年。公元前60年,汉朝设西域都护总领西域事务、监督西域各国,并负责向中央汇报西北绿洲王国的情报。这些情报后来都被载入正史。据《汉书》记载,龟兹人口为81317人,是北道最大的绿洲。[12]这一地区汉朝统治的遗迹很少,在都护府所在地今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策大雅乡曾发现一座汉朝的遗址。[13]公元46年,邻近的绿洲王国莎车攻陷了龟兹。
西域王国间的不停征伐意味着汉朝只能时断时续地控制自己的驻地。公元91年,汉朝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他成功地又一次控制了龟兹,并把白氏家族的一员扶上王位。但仅仅二十年不到,107年时西域复乱,汉朝再一次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从这时起,白氏家族开始在龟兹掌权,他们有时独立,有时依附于周边的强权,其势力延续了几个世纪。
到鸠摩罗什降生的4世纪,龟兹已经是著名的佛学中心。译师中有几位姓帛②,大多来自龟兹的王族。有纪年的最古老的龟兹佛教材料的年代为3世纪[14],当时流行说一切有部——这是小乘佛教的一部。[15]龟兹人通过印度传法僧来了解佛教。印度的影响在3世纪和4世纪最大。鸠摩罗什及其父母可以在印度与龟兹之间轻松往来便是明证。

纪念鸠摩罗什
巨大的鸠摩罗什铜像在克孜尔石窟前欢迎四方来客,由此可见这位译师直到今天依然赫赫有名。因为鸠摩罗什没有肖像流传下来,所以人们对于他的实际相貌一无所知,雕刻家只能全凭想象创作。(渡边武供图)
来源 Takeshi Watanabe, 7/25/06.
龟兹为未来翻译家的成长提供了完美的环境。这个绿洲王国与犍陀罗关系紧密,因为顺着横穿塔克拉玛干的河流可以抵达南道的莎车和于阗绿洲,从那里翻山即可到达犍陀罗。鸠摩罗什的父亲是一位印度高官的儿子。他离开犍陀罗来到龟兹学习佛法。在龟兹,他被迫娶了龟兹王的妹妹,生下了鸠摩罗什。因此,鸠摩罗什从小就讲犍陀罗语和本地的龟兹语。
鸠摩罗什的母亲是虔诚的佛教徒,她不想过家庭生活。鸠摩罗什七岁时,她要求出家。被丈夫拒绝之后,她绝食了六天。丈夫终于让步,她便带着鸠摩罗什出家为尼。龟兹是印度以外少数几个女人可以出家的地方。一份佛教文献列出了龟兹的四所尼姑庵,分别有尼姑50人到170人不等。[16]
在龟兹学习之后,鸠摩罗什跟着母亲来到犍陀罗跟随一位小乘法师学习经文。随后鸠摩罗什至疏勒(今喀什)师从一位大乘法师继续深造。之后他回到龟兹,并使一些僧人转皈大乘。尽管后来的佛教材料把大乘小乘描绘得泾渭分明,但在鸠摩罗什的时代,大小乘的差别并没有那么明显。年轻人出家,从某僧处受法戒,也就进入了某个传承派系。某人属于某个派系,例如说一切有部,并不意味着此人一定是小乘或是大乘,而是可以像鸠摩罗什一样先学小乘经典再学大乘经典。大乘僧与小乘僧共处一寺并不为奇。[17]
然而大乘和小乘在某些教义上的差别很明显。关于吃肉,小乘认为只要不是特意为自己宰杀的肉就可以吃,大乘则戒荤腥。后来有人经过这里时注意到龟兹僧吃肉、葱和韭菜(这些都属于大乘禁食的荤腥),由此判断龟兹僧绝大部分是小乘。[18]
384年,鸠摩罗什差不多四十岁时,他的家乡龟兹被吕光攻破,对当时情形的记载被保留了下来(见史料16)。[19]攻下龟兹之后,吕光把鸠摩罗什送至自己所据的凉州以示虔敬。尽管鸠摩罗什已经受了色戒,但是吕光认为鸠摩罗什这么伟大的学者不留下子嗣实在太可惜了,于是就把鸠摩罗什灌醉,然后派一名年轻姑娘侍寝。按照鸠摩罗什传的作者记载,这是他一生中三次破戒的首次(见史料17)。
401年,在后秦统治者姚兴(394—416年在位)的命令下,鸠摩罗什第二次被掳走,并被送到了长安。鸠摩罗什又主动讨要了一名女子,又一次破戒,并和她生了一对双胞胎。姚兴希望鸠摩罗什能够有自己的“法种”,便让他在寺院旁边建立家庭,跟几个小妾同住。[20]因为高僧传记受既定模式的影响很大,鸠摩罗什的不同传记之间的记载有出入,学者们并不确定这三件事是否真正发生过。尽管如此,这些不同记载在一点上是相同的,即公元400年左右时僧人破色戒并不会让在家人感到非常吃惊。[21]
鸠摩罗什破戒丝毫不影响他作为佛教法师的成就。401年,鸠摩罗什受姚兴委托主持译场,一直干到413年去世。他译的佛经直到今天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22]鸠摩罗什的译本中最有名的要数《妙法莲华经》。这是一部大乘经,里面贬斥了小乘教法,并向信徒保证,即使只听到此经的一偈也能成佛。[23]
尽管之前也有人翻译过此经,但是因为经里面有太多佛教用语,只有学过梵语的少数中国人才能看懂。大多数早期佛经都是由印度来的佛僧一边背诵一边口头解释,经弟子笔录形成译本。这种翻译方式会造成很多错误,因为师父读不懂弟子们的翻译,弟子们也不确定是不是真正明白了师父的意思。[24]
让翻译难上加难的是,梵语和汉语分属两个不同的语系。梵语属于印欧语系,与其他古代印欧语系语言一样,梵语的曲折变化特别丰富。动词和名词根据其在句子中的功能可以有很多形式。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语法上要简单得多,动词和名词没有形式变化,词序决定句义,因此经常产生歧义。5世纪的语言学习者最想要的就是一个双语文本,里面每句话都有两种语言对照。
鸠摩罗什最大的发明是创立了译场,里面的译员可以对照印度原文核对译本,翻译的功劳都归在鸠摩罗什名下。这些译本以其可读性著称,即使完全不会梵语也能读懂。鸠摩罗什行文优美流畅,以至于读者们都更爱他的译本而不是后来更精准的译本。
鸠摩罗什和其他译师成功地让汉语读者读到了数以千计的佛教作品。他们还发明了一个一直沿用至今的系统,即用汉字音译外语单词音节。这是今天汉语拼音的拼写系统的基础,用这一系统可以把Coca Cola译成“可口可乐(Kěkǒu Kělè)”,把McDonald’s译成“麦当劳(Màidāngláo)”。鸠摩罗什的发音为kuw-ma-la-dzhip。[25]因为汉语许多世纪以来的语音变化,今天他的名字用拼音写作(Jiūmóluóshí)。[26]
这种用汉字音译梵语的做法也让汉语本身发生了变化。据宾夕法尼亚大学汉学家梅维恒教授估算,汉语大概因此增加了35000个新词。不仅包括“般若(智慧)”这种佛教术语,而且包括“刹那”这种日常词汇。与梵语的接触还让中国人更好地了解到自己语言的语音结构。举例来说,中国人之前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语言是有声调的。这可是今天学汉语的学生第一天就会学到的。直到鸠摩罗什的时代,中国人才开始系统地了解自己语言中声调的性质。[27]
鸠摩罗什及其同僚在长安译经的同时,整个西域的其他译师也在进行这项把梵语佛经翻译为本地语言的长期事业。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本地语言是龟兹语。该语言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与距离龟兹不远的焉耆的语言有区别。与研究丝路的很多课题一样,解读这门语言的过程充满了挫折、弯路和争论。全世界的学者花了近一个世纪的工夫才最终明白这两种语言的关系。
1892年,已经失传的龟兹语尚存于世的迹象首次出现。那一年,俄国驻喀什领事买了一件用梵语学者熟悉的婆罗米字母写的文书,但文书的语言肯定不是梵语。这件文书困扰了学者们很多年。首先,虽然随后发现了很多同种语言的文书,但能用来研究的材料还是少之又少。存留至今的绝大多数材料都是来自不同文本的散页,或者是写在木头上的商贸、行政文书。此外,几乎所有这些文书都没有纪年。[28]
1908年,两位德国学者埃米尔·西格(Emil Sieg)和威廉·西格灵(Wilhelm Siegling)用一件双语文书破解了这门未知的语言。他们所用的双语文书是一份学校作业,上面用梵文逐字标注了作业中的未知语言。西格和西格灵并不知道哪件出土文书中有这种语言的名字,因此他们基于一篇很短的后记(colophon)给这种语言取了个名字。(后记中一般记有作品标题、章节标题、作者,有时也有抄写者。此外还可能有抄写日期和雇人抄经的出资人。)
这篇后记是《弥勒会见记》(Maitreyasamiti)的回鹘语译本的后记。回鹘语是一种突厥语,是主要生活在今天蒙古国的回鹘人的语言,9世纪中叶随着回鹘人西迁而进入了塔里木盆地。[29]后记中说这件作品先从“印度语言”译为“Twghry”语,又从“Twghry”语译为回鹘语。[30]西格和西格灵判断“Twghry”一定是那门未知语言的回鹘语名字,因为《弥勒会见记》只有回鹘语和未知语言两个版本存世。这个判断可以说是非常合理的。
西格和西格灵进而认为Twghry是回鹘语对吐火罗一词的翻译。吐火罗人是古希腊人记载过的一支古代民族,他们生活在阿富汗的巴克特里亚地区,即今阿富汗北部马扎里沙里夫周边。此外,他们还认为吐火罗人就是创立了贵霜王朝的月氏人。西格和西格灵接受汉文古籍中的记载:公元前200年左右,月氏人分为两部,即在甘肃的小月氏,以及在费尔干纳的大月氏。然而西格和西格灵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所谓的吐火罗语文书是在西域北道发现的,这里离推定的月氏人的故乡甘肃很远,离月氏人后来定居的费尔干纳盆地也很远。[31]
后来的研究者把正史中月氏人迁徙的记载和近来的发现调和起来。有人说,月氏人的家园并非如正史所说局限于敦煌地区,而是扩展到整个新疆和甘肃。[32]另有人说,月氏人离开甘肃时讲的是吐火罗语,但到了阿富汗就改讲属于伊朗语族的大夏语。[33]此外,当月氏人的后代来到尼雅时,他们讲另一种语言——犍陀罗语。这是一种印度系语言而非伊朗语。所有这些假设都让人更加怀疑传统史书中记载的月氏人迁徙,以及吐火罗语这一命名的准确性。
1938年, W. B.亨宁(W. B. Henning)为Twghry提出了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解释。他发现,有“四Twghry”(有时没有末尾的y)这样一个词组出现在9世纪早期的粟特语、中古波斯语和回鹘语的一些记载中。[34] “四Twghry”指北庭(回鹘语名字是别失八里,位于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庭镇)、吐鲁番、焉耆之间的区域,并不包括龟兹。亨宁提出, Twghry语本来通行于塔克拉玛干北缘一个东起吐鲁番和北庭、西至焉耆的地区,但是这种语言先在吐鲁番和北庭消亡,继而在焉耆也消亡了,并被直到今天仍通行于新疆的维吾尔语取代。[35]亨宁的说法并未被广泛接受,但其优势是解释了Twghry语文书的地理分布。
实际上,我们知道月氏人的官方语言是大夏语,即一种用希腊字母书写的伊朗语。[36]因此,吐火罗语是个误称。没有现存证据显示阿富汗吐火罗斯坦地区的人操库车文书中的那种“吐火罗语”。尽管西格和西格灵把Twghry语和阿富汗的吐火罗人联系起来是错误的,但“吐火罗语”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
西格和西格灵把文书中的语言分为方言A和方言B,这两种方言现在被认为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分别被称作吐火罗语A和吐火罗语B。这两种语言同属印欧语系,与梵语一样有复杂的曲折变化,动词和名词根据其语法功能有词尾变化。吐火罗语A和吐火罗语B有很多相同的词汇,这表明二者来自一个共同的源头。
20世纪美国杰出的语言学家乔治·谢尔曼·雷恩(George Sherman Lane)认为,这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别巨大,二者一定彼此独立发展了很久,即使没有一千年,最少也有五百年。[37]吐火罗语A和吐火罗语B实际上确实差别较大,类似于今天的法语和西班牙语,因此二者之间不能互通。[38]
考虑到这两种语言通行于塔克拉玛干北道,我们很容易认为它们与印欧语系的印度-伊朗语族有很多共同点,因为后者通行于邻近的印度和伊朗。但是,相较于伊朗诸语言或者梵语一系诸语言,两种吐火罗语与德语、希腊语、拉丁语和凯尔特语更接近。爱达荷大学英语系教授道格拉斯·Q. 亚当斯(Douglas Q. Adams)认为,“根据其与日耳曼语、希腊语等的关系,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把吐火罗人‘放置在’晚期原始印欧人的世界中,比如在(北边的?)日耳曼和(南边的?)希腊之间”。[39]亚当斯的谨慎措辞表明,在久远的过去,也许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之间,之后会发展为吐火罗语A和吐火罗语B的原始吐火罗语从原始印欧语中分离出去了,当时操原始日耳曼语和原始希腊语的人也正在从原始印欧人中分离出去。我们对于古代迁徙实在所知甚少,用语言证据来重构迁徙危险重重,我们无法指明古代的吐火罗语使用者在进入塔里木盆地之前的所在地。也许在中亚曾出现过跟吐火罗语很接近的语言,但没有材料留下来。
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中亚和东亚的民族总在迁徙,某地通行的语言也经常因此而改变。汉文史料记载了公元前2世纪由匈奴扩张导致的各民族接连迁徙、6世纪时突厥的兴起,以及9世纪时回鹘人迁入新疆。[40]突厥是今天土耳其人的远祖,回鹘人讲的语言是突厥语的一种。类似的部落迁徙在没有史料记载的远古也很容易发生。中亚和东亚的常态是语言的变动而不是延续。
从西格和西格灵起,语言学家们逐渐弄清了吐火罗语A(焉耆语)与吐火罗语B(龟兹语)之间的关系。2007年,奥地利科学院的玛尔灿(Melanie Malzahn)教授统计了现存的所有焉耆语写本。整页和残片加在一起总计1150片。[41]其中整页的写本不到50件。[42]
383件焉耆语写本来自舒尔楚克(Shorchuk)的一个抄经房,这个地方位于从焉耆到库尔勒的大路西南。[43]现存文书中从未提及语言本身的名字,但因为几乎所有文书都发现于焉耆附近,而焉耆的梵语名字是Agni,所以学者们便把这门语言称为焉耆语(Agnean)。[44]在下文中我们也用这个名字。现存写本表明,在公元后的头几个世纪,焉耆语曾通行于焉耆和吐鲁番地区,那时西方的波斯人首次把佛教引入当地。
焉耆语最长的写本有25页,与大多数残存的单页相比,这件写本前后连贯,没有大的阙文。这是一个本生故事,情节和《葛蓓莉娅》(Coppélia)③的故事差不多。主角是位名叫Punyavan的王子,这是个梵语名字,意为“有福”。他和他的四个兄弟争夺王位。四个兄弟分别叫有力、有巧、有貌、有智。焉耆语版本的故事跟梵语原版和后来的汉语版、藏语版都不同,五个王子争位的情节只占了17页中的2页,剩下的篇幅都是五个王子长篇大论地描述自己的特长。
王子有智讲的故事是这样的:一位工匠制作了一个机关女偶,并把女偶放在了一名年轻画师的房间里一夜(见史料15)。年轻的画师爱上了女偶,可当他伸手去摸时,女偶碎了。画师因此用墙上的一条绳子上吊自杀了。工匠发现画师自杀,便招呼邻居和官员过来。等人到了,他准备把挂着尸体的绳子剪断。就在这时,画师从墙后走了出来,对工匠说:“一画一画师,怎会分不出?”画师以假乱真的自画像是他对机关女偶的回应,毕竟女偶没有智慧。[45]这个令人难忘的故事体现了智慧的优势。故事的听众很有可能是寺院里的学僧。
德国人在吐鲁番附近的胜金口(Sängim)发现的一件写本很清楚地展示了两种吐火罗语的不同用途。写本的正文是焉耆语,附有19条龟兹语和2条回鹘语的注解。对此雷恩解释道:“这件文本很明显是一个新来的人在注解吐火罗语A[焉耆语],至少其经堂语是吐火罗语B[龟兹语]。此人并不熟悉当地旧经堂语。此人的母语也许是突厥语[回鹘语]。”[46]在6世纪到8世纪,焉耆语仅有僧人使用,且只用于书面。现存的焉耆语文本中没有方言差别,这意味着该语言在当时已经基本僵化。在寺院以外,焉耆和吐鲁番地区的人要么讲汉语,要么讲回鹘语。
龟兹语与焉耆语有一些很重要的差别。龟兹语中有方言差别,这是语言在不同地方长时间发展的产物。龟兹语还可按时间分为如下几个阶段:早期龟兹语、正统龟兹语、晚期龟兹语,以及俗龟兹语。[47]1989年,龟兹语研究的领军人物,法国学者乔治-让·皮诺统计了龟兹语文书,总共3120件。[48]加上近年才能看到的柏林残片后,他已经把这个数字增加到了6060。然而,完整纸页的总数不超过200。[49]
20世纪初,伯希和收集了2000件左右龟兹语残片,其中大多出土于库车以南20千米的都勒都尔·阿护尔(Duldur Aqur)遗址的一座寺庙周围。[50]与焉耆语文书不同,这些文书中出现了其所使用语言的名称——龟兹语。[51]龟兹语的使用范围较广,包括塔克拉玛干的整个北缘,其核心地区是龟兹,最东至吐鲁番,也包括焉耆语的核心地区焉耆。
根据伯希和的笔记,很多汉语和龟兹语的材料都来自同一座书房,由于书房的一堵墙塌了,很多文书得以保存下来,但后来的大火又将其严重损坏。伯希和在不止一个地方发现有文书尚存。宗教文书来自寺院的佛殿和佛塔,行政文书则肯定来自寺院的角落。[52]
5世纪末,龟兹人已经在使用龟兹语。此时的西域进入了一个极其混乱的时期,不同的部落联盟在争夺主要商路的控制权。这些部落包括柔然(中文又作芮芮、蠕蠕,在欧洲则称之为阿瓦尔人)和嚈哒。柔然在征服了龟兹和焉耆之后瓦解,于552年被突厥取代。突厥人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征服了龟兹和焉耆,并让当地统治者继续掌权。552年之后,突厥部落联盟建立者的弟弟领军向西征伐,征服了新疆的一部分,以及一直延伸到黑海的广大土地。兄弟二人最终建立了一个有东西两部的汗国,哥哥掌管东部,弟弟掌管西部,从属于哥哥。时过境迁之后,这样的关系仅仅流于形式。直至580年,独立的东西两个汗国逐渐形成。[53]龟兹王以西突厥可汗为宗主,向其进贡,必要时还提供军队。
汉文史书记载,6世纪到8世纪期间,龟兹一直由白氏掌权。史书的编纂者经常照抄前朝史料。他们都说龟兹很富庶,送来过昂贵的贡品。《魏书》编纂于551年到554年,其中首次记载龟兹人以银币纳税:“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钱入官。”同书还记载龟兹有一种罕见的自然资源:“其国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数里入地,如䬾餬,甚臭,服之发齿已落者能令更生,病人服之皆愈。”这种神秘的物质是石油。[54]今天的库尔勒正是中国最重要的油田之一。
该史书还列出了龟兹的特产:细毡、烧铜、铁、铅、麖皮(用来制靴)、氍毹、铙沙(冶炼和染布时用的重要物质)、盐绿、雌黄、胡粉(化妆用)、安息香、良马、犎牛等。[55]629年玄奘经过龟兹时说这里的人使用金币、银币和小铜币。[56]
尽管所有史料都说龟兹用银币,但目前只有铜币出土,大概后来找到银币的人都把银币化掉自己用了。伯希和找到一个有1300枚钱币的陶罐,其中1105枚都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币章部,包括汉朝及3世纪的几个政权的钱币,但没有唐朝钱币。负责这部分收藏的馆员弗朗西斯·提耶利(François Thierry)把这组钱币的年代定在3世纪到7世纪之间,并认为六七世纪的可能性最大。[57]钱范和两个铸铜作坊遗址的发现,表明龟兹的白氏王朝完全有能力自己铸造铜币。
另外,龟兹还出土过一些龟兹语的账目,其中记录了寺院的支出、进账和结余,显示寺庙用铜币付账。[58]这些账目中还包括在仪式上表演的乐师使用的糖酒花销。寺院也买进必需品,比如仪式上要用的油,去磨坊磨谷子也要付钱给磨坊主。
寺院还常收到实物。有些施主会捐献食物供给僧人及替寺庙种地的依附民。村民们会把羊送给寺庙,有时是为了抵债。龟兹语中跟羊有关的词汇很丰富,无论雄雌,比如羊羔、成年羊、老羊(这个龟兹语词的字面意思是“大牙”,因为成年动物会长出终生不脱落的中央门齿)。[59]在一笔交易中,寺院长老们用两只山羊换得230斤大麦,用一只绵羊换得180斤小麦。大麦和小麦被用作货币,而没有任何一种钱币被提及。这些寺院的账目只提到了绿洲本身出产的物品,让人觉得寺院基本上自给自足,并未进行任何长途贸易。
从6世纪到8世纪,龟兹语显然还是活语言,寺庙的僧官用其记账,国王用其下令,历史学家用其写书,旅行者用其题字,信徒用其标注他们给寺庙的供品。此外,还有说书人用龟兹语讲佛教故事。如同之后的汉语变文,这些故事在散体和韵体之间变换。韵体部分前标有曲调名,告诉说书人应该唱哪个调子。[60]在著名的佛传故事中出现了三个词:“此处”“随后”“重新”。(佛传故事讲的是佛陀降生、奢华童年、出宫、见人间四苦,以及最终悟道。)同样,这三个词也作为画的标题出现在克孜尔110窟和库木吐拉34窟中故事画下方的格子里。当说书人讲解画中故事时,会指着一处说“此处乃……”。[61]焉耆语消亡之后,龟兹语还有人讲。不过在公元800年后,龟兹语就没人再用了。[62]
有些龟兹语文书的内容并非与佛教相关,而是有关更世俗的贸易。皮诺发表了伯希和发现的一组精彩的龟兹语文书。这组文书描述了进出龟兹的商队。1907年1月,某个当地居民给伯希和带来了从盐水沟不远处的佛教遗迹中发现的六块木板,上面写有婆罗米字母。[63]伯希和随即前往夏德朗附近的一个还在使用的征税站。夏德朗是库车北山里的一个小地方,扼守着通往拜城的山口。在山顶一座塔楼20厘米厚的积雪下面,伯希和发现了130件过所。
这些过所是龟兹官员清点商队人畜数量之后给商队签发的通行文书,其中并未记录商队运送的货物。在每一个关卡,商队要上交旧过所领得新过所,伯希和在盐水沟找到的一百多枚木简就是商队交上来的旧过所。
尽管龟兹地区广泛地使用纸,寺院账目和信件也是写在纸上的,但这些过所是用更便宜的杨木制作的。过所大小不一,平均10厘米长、5厘米宽(可参考本章开头的照片)。与在尼雅发现的佉卢文材料类似,这些龟兹语文书由两部分拼合而成。一枚或几枚木简插在一个木盒子里,这样一来从外面就看不到里面的内容,只能看到驿站长官的名字。[64]
尽管这些过所大小不一,但其内容都遵循一个固定的格式:签发过所的官员的姓名、接收过所的官员的姓名和地址、介绍性的问候、过所持有人的姓名。接下来是商队成员,先是男人,再是女人,然后是驴、马和牛。数字用非简写的形式,表明这是正式的行政文件。过所以祈使句结尾:“准许通过。如果其人马数多于此处所列,则不准通过。”最后写出年月日(以龟兹王在位年纪年)和保人证词。其年代在641年到644年间,这是龟兹王苏伐叠(624—646年在位)在位的最后几年。这些过所记录了政府对商队的严密管控,商队只能按照指定路线前行。
皮诺做了一个很有用的表格,列出了每支商队的人数和牲口数。13支有明确人数的商队中,9支少于10人,另外4支分别有10人、20人、32人和40人。牲口最多的有17匹马,由8个人带着。因为80号过所残损,我们不知道这一队40人带了多少牲口。驴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在现今的新疆也是如此。有些商队只有人和驴。两件过所列出了随行儿童,另外两件列有侍从僧,这些人被允许帮其他僧人做一些佛教戒律禁止的事情。[65]有一支商队(64号过所)全由女人组成,只有领队是男人。女人(以及驴)的数量已经模糊不清,无法识读。可以想象,这些女人正前往龟兹的女奴市场,并在那里被卖掉。正史中也提到过这个女奴市场。尽管过所中并未指明商队携何种货品,但这些过所说明龟兹王对进出龟兹的商队严密监控,确保商队在既定路线上行进。

资料来源:Georges-Jean Pinault, “Épigraphie koutchéenne: I.Laisser-passer de caravanes; II. Graffites et inscriptions”, in Mission Paul Pelliot VIII.Sites divers de larégion de Koutcha (Paris: Collège de France, 1987), 78。
这些文书很重要,因为很少有史料具体讲到商队的规模大小。《周书》讲的是北周的历史,成书于636年,里面讲到一支前往凉州的商队有“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66]这发生在隋统一中国之前,当时旅行还很困难,商人们必须结成大队人马才能出行,还要经常雇用保镖以保障安全。龟兹过所显示,7世纪时商队旅行已经常规化。因为道路安全,小型商队也能出行。
汉文正史、钱币和龟兹语文书这三类史料都描绘了当地繁荣的经济状况,其中既有货币经济也有自然经济。648年,唐朝军队攻下龟兹。龟兹王白氏从西突厥臣属变为唐朝子民。龟兹是安西都护府的治所,管辖安西四镇。龟兹是四镇之一,另外三镇分别为于阗、疏勒、焉耆(679年到719年,以碎叶代焉耆)。[67]在之后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唐朝断断续续地控制着西域。和之前的汉朝一样,唐朝也在西域驻军。但唐朝在西域推行跟中原一样的行政系统,龟兹都督府的结构跟内地的州一样。都督府下设州,州下设县,县下再分为乡(农村地区)或坊(城镇地区)。
研究唐朝统治时期龟兹的最佳材料是伯希和在库车南边的都勒都尔·阿护尔佛寺遗址发现的一批文书,共有214件汉文残片,很多被火烧过,非常残破。其中最早一批的年代为690年至700年,此时唐朝统治龟兹已有五十年之久,政治局势动荡不安。7世纪末,青藏高原的吐蕃人建立的帝国不断扩张,670年开始跟唐朝争夺西域,直到692年唐朝才重新控制了龟兹。[68]唐朝稳定统治五十多年之后,粟特突厥混血的安禄山起兵,差点推翻唐朝。唐朝直到763年靠回纥军队才打败了叛军。
尽管唐朝被大大削弱,唐军也从西域撤回,但唐朝的军事据点在安西都护府的领导下一直设在龟兹。从766年到至少781年,郭昕一直是安西都护府的最高领导人,其驻地在龟兹,但是他与朝廷的联系被切断了。[69] 781年,郭昕派出使者与朝廷重建联系并继续统治当地。790年,吐蕃征服这一地区,但在考古材料中几乎见不到吐蕃人的身影。9世纪中叶,回鹘人攻下龟兹并一直掌权到13世纪蒙古兴起。[70]
都勒都尔·阿护尔遗址出土的汉语文书的年代从唐朝强盛的7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792年,唐朝在这一年最终失去了对龟兹的控制。[71]与龟兹语宗教文献和寺院账目不同,汉语材料也包括世俗内容。这些文书出自驻扎在龟兹的唐朝士兵之手,有家信,也有颂扬死者英勇的三则讣告。一位忏悔的信徒列出了当兵期间违反过的佛教戒条:饮酒、吃肉、破斋、毁寺,以及伤害众生。[72]这些材料所涉及的内容多种多样:僧人在寺院中诵经、女子写信、农田大小、道教仪式中用了多少面幡子,以及一位官员的政绩考课。[73]这些文书显示,此处有一个独立的唐人聚落,很可能居住着士兵及其家眷。[74]
与龟兹语的过所一样,这些材料也记录了商队的活动。有些寄信人利用商队寄信。有位寄信人明显在赶路,他的信写得非常仓促,以至于其中有很多重复内容,为的是及时把信交给回龟兹的一队人马。[75]
这些文书中的主要交易物品是马。唐人从龟兹以北的游牧民手里用1200斤铁或者约1000尺布买马。有一件文书记载了买马时付给马政官员的粮食种类(与大豆、麦麸或大麦混合的小麦粉)及数量。[76]驻军和征伐需要用马,驿站和邮政也需要。[77]有一封马贩的信写到有一匹马痊愈了。从其他材料可知,无论是从撒马尔罕地区来的粟特人还是其子孙,都在供给唐军马匹这件事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都勒都尔·阿护尔残片中包含了一些粟特人的微弱痕迹。[78]与楼兰戍堡的文书一样,这些文书表明当地有贸易存在,但是这些贸易仅仅是唐朝官员购买自己所需(绝大部分是马)。这些文书非常残破且难以解读,它们主要证明了当地有政府管控下的贸易存在。
与政府管控下的贸易相一致的是,都勒都尔·阿护尔文书中经常提到钱币,证明当地有货币经济。个人可以在交易中使用钱币。一名白丁为了免除徭役支付了1000文,另一名付了1500文。一份清单列出了举债人的名字和债务:4800文、4000文(可能更多)和2500文。[79]考古学家在库车的其他遗址发现了11份汉文契约,其中保存最完好的是3份借据,里面讲每位举债人都借了1000文,之后以每期200文分期偿还。[80]
是谁、为了什么铸造了这些钱币?有些罗马史学者指出,国家最有可能是钱币的制造者,因为国家要用钱币支付士兵军饷。其他人指出,如果当地没有市场,士兵也用不着钱币。[81]唐朝征税有三种形式:货币、粮食、布匹(经常是固定长度的丝绸)。国家发放的大量军饷让龟兹全境有充足的货币。
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从龟兹撤军,当地的钱币流通也戛然而止。龟兹官员因此开始自己铸币,这种货币劣于唐朝货币。他们用开元通宝做出钱范,把“开元”二字换成新的年号,比如大历(766—779年)、建中(780—783年)。这些新字比较粗糙,有时还有错误。龟兹铸造的钱币另有一些特点有别于中央政府所铸钱币。因为钱范没摆正,钱孔有时不是方的而是八边形的。铸钱用的铜也比中原用的更红。新疆发现了1000枚这样的钱币,其中800枚来自库车地区。中原地区只发现了2枚。[82]很显然,这些钱币基本上只在西域流通。尽管龟兹与唐的联络被切断,当地统治者依然需要用钱币给士兵发饷。
诚然,都勒都尔·阿护尔遗址发现的汉语材料非常有限,一共只有208件,其中很多只有几个字而已,但这些文书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童丕把这些文书译成了法语,他总结道:“由大谷光瑞、伯希和收集的都勒都尔·阿护尔汉语文书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其中没有商业文书。没有商品清单,没有盐水沟附近驿站发现的那种商队用的过所。只有很少几件契约,而且看上去都是农民之间的交易。”[83]尽管这些文书种类各异,但是里面没有提到任何传统观念中丝绸之路上该有的东西,也没有带着大宗商品跋涉千里的商人。童丕认为,龟兹是个商贸中心,但是经过这里的商人住在城里或者绿洲之外,总之不在都勒都尔·阿护尔,因为这里没有出土过商业文书。
丝路上有些遗址出土了丰富得多的文书,但和都勒都尔·阿护尔一样,都没有反映长途贸易。本章的焦点,即库车出土的焉耆语、龟兹语和汉语文书,肯定是本书讨论的所有出土文书中最零散、残损最严重的。库车地区出土的汉语和龟兹语文书全部加在一起不过一万片,其中只有几百件保存较好,可以解读。龟兹有贸易,正如过所所示,政府官员紧密监督着贸易,也如都勒都尔·阿护尔遗址出土的唐朝军营汉语文书所示,唐朝军队对马的需求是贸易的重要部分。即便在军事冲突不断的8世纪末,当地统治者还在铸钱,这表明贸易和军队驻扎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库车出土的材料尽管不全面,但其表现出来的却与想象中那种带有传奇色彩的丝路贸易不同。这些文书中没有民间商人进行的长途贸易,却表明中原王朝的军队对丝路贸易有很大贡献。当这些军队在西域驻扎时,钱币、粮食、布匹这三种形式的货币就会流入该地区。军队撤走之后,由当地旅行者和小贩维持的小额贸易便重新开始了。
(乔治-让·皮诺慷慨地为本章提供了很多详细的评论,庆昭蓉非常友善地为本章初稿提出了修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