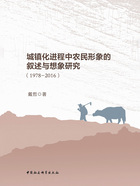
第二节 “为生民立命”的李铜钟:吃饱肚子的合法性
1978年安徽小岗村自发实行土地承包,分田到户,对上实行隐瞒,对下要求农民们保密。这在中国的乡村改革历史上成为一个著名而重要的事件。这样的一个由农村实际改革的要求所产生的历史事件,带动了80年代的改革开放。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公开肯定了小岗村“大包干”的做法,继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得到了不断的稳固和完善,也使得大量的农民摆脱了贫穷的处境。而文学也有力地介入其中——从对刚刚过去的历史的否定(伤痕文学),转向了对未来生活的重新想象。农村改革为这种新的想象提供了新的实践的空间,作家们塑造了一系列如梁三老汉一般怀揣着自己为自己劳动、做个人发家梦的农民形象,与梁三老汉所不同的是,他们的这一梦想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和实现,所以我们可以将这些农民形象称为“小生产者”。但是,有一个形象非常与众不同,这就是张一弓1980年所发表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的李铜钟。从较为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李铜钟是一位60年代“困难时期”的村委党支部书记,并不能被纳入“小生产者”这一范畴。更进一步而言,这篇小说也不能被算作反映乡村改革的小说。但毋庸置疑的是,李铜钟这个人物形象以及围绕其展开的文学叙述,以其特有的方式,凸显了小生产者农民形象出现的历史必然性。与此同时,经由李铜钟这个人物的故事,可见《创业史》中所确认的集体化的合法性如何遭到了文学叙述上的解构,农民重新回到了“土改”模式。在这个意义上,李铜钟这一农民形象也参与到了80年代的乡村改革话语中。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讲述的是“困难时期”,李家寨书记李铜钟,违反“国法”,私自动用国库粮食,挽救濒临饿死的村民们的故事。小说并没有将饥荒仅仅归因为天灾,而是将矛头直指人祸,即坏干部杨文秀,他为了对上邀功,欺瞒谎报粮食产量,导致了饥荒的发生。这样的一个故事和人物其实有原型可考。小说的背景源自河南信阳——60年代饥荒的重灾区。当时的河南信阳地委书记隐瞒了数据,导致了饥荒的严重蔓延。《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来结构故事,使得这个故事具有了极强的震撼力,有人看完曾经表示,“灵魂受到震动……无法制止自己的泪水夺眶而出,痛苦不已”。[22]这个故事,无疑对集体化的合法性进行了某种质疑和解构,而这又恰好与作者写作的年代——80年代乡村正在经历的乡村变革形成了呼应。但是,张一弓并没有直接从集体化存在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来展开讨论,而是从对农村干部李铜钟这一人物塑造上入手,经由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冲突,从而潜在地质疑甚至解构了集体化的合理性。事实上,这个人物身上其实有着河南的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的影子。在那个困难的历史时期,焦裕禄顶住上面的压力,坚决放县里的灾民出去要饭。但是在当时的语境中,因为害怕影响地方形象,村民外出要饭是不被允许的。那么具体到文学中,张一弓如何塑造李铜钟这个人物形象,并使其参与到解构集体化的过程中去呢?
张一弓征用了一个最具身体感觉的符号——饥饿,同时将“饥饿”放置在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冲突中展开叙述,而且此处所论及的个人,涉及个人生命。所以李铜钟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为生民立命”的李铜钟。有关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的文学叙述,在20世纪60年代便早已出现,比如《夺印》《艳阳天》等,在这些小说的叙述中,国家和集体的地位一定是排在个人之上的。但是李铜钟对于这个排序进行了质疑,而质疑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饥饿,是为生民立命。所以,我们会看到小说中出现了很多关于“饥饿”的描述。比如小说第二部分“春荒”开头便写道:“自从立春那天把最后一瓦盆玉米面糊搅到那口装了五担水的大锅里以后,李家寨大口小口四百九十多口,已经吃了三天清水煮萝卜。晌午,‘三堂总管’——三个小队食堂的总保管老杠叔,蹲在米光面净的库房里,偷偷哭起来:‘老天爷啊!嗳嗳嗳嗳……你睁睁眼吧,……你不能叫俺再挎要饭篮,嗳嗳嗳……'”[23]李铜钟在老杠叔的屋外听到老杠叔大喊:“花她娘……人死如灯灭,还做那啥送老衣?……你要心疼我……就拽一把棉花套子,叫我啃啃……啃啃……”[24]而发生饥荒的原因是什么?是全国试图以“大跃进”的方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号召,所以“带头干部”杨文秀向大家宣布他所在的公社将要两年内进入共产主义,李家寨也没能逃脱“带头书记”带来的一场灾难:“去年天旱,加上前年种麦时钢铁兵团还在山上没回来,麦种得晚,一晚三分薄……而带头书记又带头提出了‘大旱之年三不变’的豪迈口号,产量不变、对国家贡献不变、社员口粮不变。结果,两头的不变落空,只是经过‘反瞒产’,才实现了中间那个‘不变’。”[25]正因为“不变”,李家寨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饥荒。
在这样的一种境况之下,在国家和个人生命之间,难道还是国家优先吗?李铜钟毅然选择了后者,动用了国库粮,以保李家寨人性命的平安。在此意义上,“饥饿”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生理体验,反而成为一个符号,表征着某种“以下犯上”的合法性。正是因为饥饿的存在,使得李铜钟毅然地自行宣布这个自然村庄进入了阿甘本所说的“例外状态”,阿甘本指出:“法与人类生命/生活之间关系的建立正在于法与某种‘无法’之间关系的建立。简单地说,法透过自身以悬置的方式设定为无法,而将生命纳入治理。而这个悬置的设定、排除的纳入,便是例外。”[26]也就是说,当李铜钟宣布李家寨进入紧急状态,并将国法悬置,他又借用了另外一个法理用以支撑自己,即生命权高于一切。更具体而言,李铜钟的法理依据来自德性传统——民以食为天,干部要为生民立命。这样的一种德性传统,实际上既内在于中国的革命史传统中,又内在于中国历史的士大夫传统里。中国经历过很多生死攸关的时刻,最后都能够转危为安,实际上都与德性传统有关。所以在李铜钟身上,我们会看到,当他敢于宣布自己的村庄进入例外状态,并动用国库的粮食时,他依据的就是“民以食为天,干部要为生民立命”这一最根本的法理,只有这个法理才可以解释为何他敢于悬置国法而不顾。这样的一种法理和逻辑也宣布了每个人都有权决定自己能够采取哪种措施和行动。
也正是因为中国德性传统中的民以食为天、为生民立命作为最根本法理的存在,李铜钟的行为受到拥戴,即使大伙都知道这粮食是“违法粮”,“但是在大多数七天没吃一粒粮食子儿的庄稼人看来,对于他们必不可少的肠胃运动和衰弱到极限的身体来说,违法粮跟合法粮没有任何区别,或者可以说是同样的‘老好’。营养学家可以作证,玉米,无论是违法的还是合法的,它所包含的蛋白、淀粉和含热量完全相同”。[27]唯独老杠叔对吃国库粮/违法粮感到极为不安,所以他经历了剧烈的心理斗争:“违法粮同时又是救命粮,这种精神和物质的分裂,使得老杠叔越想越糊涂了。”[28]即使如此,最后他还是用民以食为天的德性传统说服了自己:“毛主席,您老人家就原谅俺一回……咱李家寨的干部都是正经庄稼人,没偷过,没抢过……铜钟是俺从小看大的,去朝鲜国打过仗,是您教育多年的孩子。……俺吃这粮食,实在是没有法子……毛主席,……当个人老不容易呀!您就原谅……原谅吧!”[29]张一弓关于老杠叔的这一叙述,具有了两层意义。第一层,老杠叔自我说服的过程,实际上再次凸显了在极端情境下“吃国库粮”的合理性;另一层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借老杠叔之口说出了“正经庄稼人”却因为“饥饿”没有办法活下去,没有办法“当个人”。这显然把矛头指向了集体劳动,集体劳动没有办法让人摆脱饥饿带来的死亡威胁,当连“做一个人”这一最基本的生存需求都没有办法满足的时候,所谓的集体化的合理性就会瞬间崩塌。类似的表述在小说中其他地方也出现过,比如李铜钟在向粮库守护者朱老庆借粮食时说:“要是李家寨都是懒虫,把地种荒了,那我就领着这四百九十多口,坐到北山脊上,张大嘴喝西北风去,那活该!可俺李家寨,都是那号最能受苦受累的‘受家’,谁个手上没有铜钱厚的老茧,谁个没有起早贪黑的跃进?他们侍候庄稼,就跟当娘的打扮他们的小闺女一样。”[30]李铜钟的这段陈述同样潜在地表征出集体劳动的问题:在集体劳动时代,饿肚子的问题并不能得到解决,甚至个体的生命也会受到威胁。
李铜钟的行为无疑是大胆的,甚至看起来有一些“反动”,所以《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在1980年底至1981年初,曾经引发了一场极为复杂的政治纠纷,河南省来人,拿着盖红章的介绍信和材料,告张一弓是‘文革’参与夺权的造反派头头,‘震派’人物,指斥小说如何攻击了社会主义现实”,[31]但事实并非如此。李铜钟虽然触犯了“国法”,私自动用了国库的粮食,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否定“国法”,更不会否认国家和社会主义的正当性。在小说的叙述中,我们也未见李铜钟对党和国家的丝毫否定,反倒是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国家和党的信任。正如他向朱老庆要粮食时所说:“老朱,我要的不是粮食,那是党疼爱人民的心胸,是党跟咱鱼水难分的深情,是党老老实实、不吹不骗的传统。庄稼人想它、念它、等它、盼它,把眼都盼出血来了……”[32]这段话中充满了对党的深情,而李家寨出现的灾难,在小说的叙述逻辑中,党和国家并不知情,都源自干部的邀功和“反瞒产”。所以,小说除了塑造了李铜钟这样以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触法国法,甚至牺牲自己性命的农民干部之外,还塑造了另一个与之截然相反的“坏干部”杨文秀。杨文秀为了能够做出功绩,赢得领导赏识,在集体化政策的号召下,不断欺上瞒下。需要提及的是,对于杨文秀这类坏干部的描写,张一弓并没有将其放置在历史的脉络里做较为深刻的讨论,而实际对于如杨文秀般的干部的讨论应当涉及的是对中国政治实践中的对上问责制的讨论,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恰恰也离不开对上问责制。对上问责制使得地方变得更为活跃,某种意义上成为改革开放的内动力。但是张一弓仅仅把杨文秀这一个遵循了对上问责制、极为活跃的干部,描绘成一个在道德层面上的“小人”形象,这种处理方式其实是缺乏复杂性和深刻性的,不只张一弓如此,这也是80年代写作存在的普遍问题。但不可否认,这样的一种塑造方式,更加凸显了李铜钟的“对下问责”,即为村民的利益敢于牺牲自己的大无畏精神。所以某种意义上,坏干部杨文秀以及经由其显现的集体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是造成李家寨陷入饥荒的原因。而李铜钟不仅没有否认国法,同时还甘愿和敢于接受国法的制裁。
由此可见,《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通过征用“饥饿”这个极具身体感觉的符号,将李铜钟这一人物形象,放置在特殊的历史语境——“困难时期”,以及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中展开叙述,从而潜在地解构了集体化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如果说民以食为天,反过来集体化不能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求的话,那么集体化的合理性又在何处?与此同时,李铜钟这位“为生民立命”、将中国的德性传统放在第一位的好干部,在当时不仅感动了很多人,也为改革者提供了莫大的勇气。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这篇看似“伤痕文学”的小说,却可以被纳入“反映乡村变革”的小说之中,从而为20世纪80年代的乡村改革提供了文学上的支持。而“为生民立命”的农民干部李铜钟,于是也很自然地与80年代早期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形象一起为改革确立合法性。与《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相似的关于“饥饿”的叙述在文学中并不少见,只是在其他文本中饥饿更多地是以“饥饿记忆”的方式出现。比如《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中的“饥饿记忆”是通过姑父家过去的生活得以呈现的,“姑父家三口人,两个初中的庄稼人,加上姑姑的勤劳,这个家庭完全可以富裕而殷实。可是结果每年都几乎连肚子都吃不饱”,[33]这句话其实暗含了“集体劳动”不能带来温饱的事实。而现在,“姑父家的生活好起来了”,这个“好起来的现在”显然源自小说一直强调的“单干”。在当下回忆过去经历的“饥饿”,是这一时期很多小说共同的叙事模式,如何士光的《喜悦》、矫健的《老茂的心病》《老茂发财记》《老霜的苦闷》等作品也是如此。有意思的是,这样的“饥饿”或者“饥饿记忆”在合作化时期的小说中,也曾被用来证明农业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必要性,如在《创业史》《三里湾》《金光大道》等一系列作品中,作者常常是用“创业——生存”作为“饥饿——死亡”的转喻形式,显然,“饥饿——死亡”背后是历史理性的强大支撑,“创业——生存”为“合作化”等提供了有力支持。[34]所以,当合作化变得不能解决“饥饿”问题,反而带给人生存威胁甚至导致死亡时,合作化的合法性便不攻自破。
最后还不得不提及的是,在关于李铜钟的故事里,实际上存在着多种写法或多重叙述的可能性。第一种叙述的可能性:之所以出现饥荒,陷入苦难,是因为国家和集体的关系没有叙述好,那么存在的一种叙述的选择是国家可不可以向集体让利,国家如何向集体让利。正如小说中提及李家寨在饥荒时期还交了很多公粮;第二种叙述的可能性是,集体如何形成自己的力量,加强集体的建设,从而帮助村庄的村民形成对抗灾害的防御机制;第三种叙述的可能性则是集体彻底瓦解,只剩下本能——吃,从而围绕这种本能调动整个故事的叙述。很显然,张一弓选择了第三种叙述方式——集体瓦解,个人退出集体。这样的一种选择,实际上表征着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不再是重新组织和整顿村社这类集体,而是对乡村的进一步瓦解,而整个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对乡村和农民的盘剥。当然,在80年代早期的乡村叙事中,因为处在改革的初期,80年代的现代化改革对传统乡村秩序的破坏和对农民的盘剥几乎没有显现出来,而只是将集体化时代农民情感解构中被深埋和被压抑的记忆复活:包括对土地的情感,以及凭借自己的土地发家致富的记忆——这正是《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记忆,这样的记忆全部可追溯至1949年的土地改革。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也参与了对“土改记忆”的复活,重回土改模式,呈现出集体化、合作社的问题,进而展开对农民要求从集体中脱离出来的愿望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