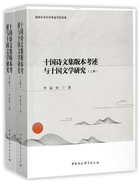
前言
十国,指历经唐末、五代和宋初,即从公元891年到979年长达89年的历史中,独立于中原王朝之外的十个割据、半割据政权:吴、南唐、前蜀、后蜀、南汉、楚、吴越、闽、荆南、北汉。
本书《十国诗文集版本考述与十国文学研究》有五项任务:一是考索十国文人著作的书名、卷数、作者、类别、内容、出处、流传、存佚和真伪问题;二是辑录十国中有诗文集善本书存世的21名文人诗文集的序跋文字和著录文字;三是考辨21人诗文集的流传过程和版本源流,并绘制《十国文人集部著作流传过程和版本源流示意图》;四是辨析十国文人生平行迹和作品真伪方面的疑点问题;五是十国文学创作述论。
一 本书的研究意义
十国文学是“五代十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唐文学向宋文学嬗变的关键环节;十国除北汉之外的九国皆处于长江以南,故十国文学是南中国地区的文学,体现着很强的地域性,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经典案例;就像十国一直被作为五代或晚唐五代的附庸一样,十国文学一直被作为五代文学或晚唐五代文学的附庸,更严重的是,即便就附庸的地位而言,十国文学被研究得依然很不全面、很不充分。所有这些,使得本书《十国诗文集版本考述与十国文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得到彰显和加强。
首先,十国文学成就突出,是五代十国文学的主体,是唐五代十国文学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文学史上“一个灿烂的时期”。先看一组数据:清康熙时朱彝尊(1629—1709)《词综》所选五代词6首(李存勖2首、和凝4首),占五代十国词入选总数148首的4.1%;清乾隆时李调元(1734—1803)《全五代诗》所含十国篇幅83卷,占五代十国篇幅100卷的83%[1],今人的统计结果与李调元的卷数安排大致相当,例如张兴武先生说唐末五代文学作品中,南方作家的作品“占总数的82%”[2];据笔者统计,《唐诗品汇》所选数量之多排名前10位的五代十国诗人中,十国诗人以93首的入选数量占五代十国入选诗歌110首的84.5%(前10名是:张乔27首、韦庄23首、罗隐10首、王贞白10首、司空图7首、贯休7首、韩偓7首、崔道融7首、杜荀鹤6首、罗邺6首,其中仅王贞白和司空图是五代诗人)。可见,从词到诗,从数量到质量(入选数量的多寡一定程度上体现着质量的高低),十国文学都是五代文学的主体。再看一个数据:傅璇琮先生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所含《五代卷》(五代卷含五代和十国,而且主要是十国)篇幅656页,占全书篇幅3463页的18.9%。可见,以十国文学为主体的五代十国文学至少在篇幅上可以追步初唐文学、盛唐文学、中唐文学、晚唐文学从而成为唐五代十国文学五个阶段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很可能正是因此,清代学者郑方坤(生卒年不详,1720年前后在世)在《五代诗话·例言》中先论断说:“五代中原多故,风流歇绝,固不若割据诸邦,犹能以文学显。此朱竹垞先生《词综》标目,有五代十国之称也。”然后又将韩偓(842—914?)、罗隐(833—910)、韦庄(836?—910)这三个十国诗人称为五代十国时期的“华岳三峰”[3]。杨荫深(1908—1989)《五代文学》的说法是:“就五代而言五代(指梁唐晋汉周),那是没有什么文学可以说的;就五代而旁及十国,五代仍不愧为有文学的一个时代,而且在文学史上还可称为一个灿烂的时期。”[4]杨荫深先生说不含十国的五代,是没有什么文学可说的,而含有十国的五代,才是文学史上一个灿烂的时期,那显然是说,十国文学是文学史上一个灿烂的时期。
其次,十国文学特色鲜明,是与唐代文学、五代文学(不含十国文学)在地域、体裁、作用三方面大有不同的一段历史时期的文学。十国中北汉国的文学最弱,几乎没有研究的价值,十国文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其他九国中,而其他九国皆在长江以南。可以说,唐代文学和五代文学(不含十国文学)主要是黄河流域的文学,而十国文学主要是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闽江流域的文学,尤其以长江流域的文学最为发达。例如,吴国文学、南唐国文学、前蜀国文学、后蜀国文学、荆南国文学、楚国文学、吴越国文学这七个国家的文学分布于长江流域。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或者说从文学地域特征的角度)看,十国文学的研究价值不言而喻。五代十国文学最有成就的体裁是词。许总《唐诗史》以林大椿《唐五代词》为据统计后得出的结论是,五代词人占唐五代词人的40.4%,五代词作占唐五代词作的67.5%,但五代时间只占唐五代时间的15.2%[5]。从曾昭岷等先生主编的《全唐五代词》看,五代词占唐五代词篇幅上的65.9%。由此可知,五代十国文学在体裁上确实以词著称于文学史。对此,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评价云:“五代的文坛,以新体的诗,所谓‘词’者为主体。词人们雄踞着当代的各个文艺中心的骚坛上,气焰不可一世。”[6]杨荫深《五代文学·绪言》的评价是:“词原起于中唐,至五代而方盛,后至于宋,始更发挥光大。所以,五代可以说是词的草创时代,若不经过这一个时代,词的发展是不会有这样迅速的。所以,五代在文学史上,便永远成为一个可纪念的时代。”[7]五代十国文学尤其是十国文学是唐宋文学演变的一个关键环节,这既表现在长达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时期中文学的重心从黄河流域迁移到长江流域这一重要历史现象上,又表现在词这种新兴的诗体在经过了唐代二百余年的长期积累后终于在十国中的蜀地和南唐得到长足发展从而为词在宋代的兴盛奠定了基础这一基本事实上,还表现在十国文人诗歌的诗句对柳永、欧阳修、李清照等宋代词人的影响和十国文人诗歌侧重风情的倾向(例如后蜀国韦縠编选的《才调集》100卷)对元明清诗人(例如金代《唐诗鼓吹》和清代杜诏、杜庭珠《中晚唐诗叩弹集》)的影响上。可惜,这些现象很少引起学界的注意,连李定广先生认为唐末五代在唐代雅文学向宋代俗文学这一重大转折过程中“似乎不只是蜂腰,更是咽喉”的论断[8],也应者寥寥。
再次,十国文学的研究成果相当薄弱,许多内容的研究还是空白,是一段亟待开发的研究领域。如前所述,从数量到质量,十国文学在五代十国文学中都占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比重,是紧紧跟随在初唐文学、盛唐文学、中唐文学、晚唐文学之后能够完成承先启后作用的一段历史时期的文学,完全具有独立出来专门研究的价值和资格,“十国文学”这个名词早该应运而生了;与唐五代其他阶段的文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初唐文学、盛唐文学、中唐文学、晚唐文学、五代文学这些名词不仅常被人提起,而且还作为研究题目屡次出现,而“十国文学”这样的名词尚且未见有人提出,更不用说让“十国文学”这个名词出现在研究题目中了;退一步讲,即使不用“十国文学”这样的题目,而是将“十国文学”隐含在“五代文学”中,只要实际上对十国文学都作了研究而且研究得比较充分和深入,那就不一定非得提出“十国文学”这样的名词不可,可是,即使从隐含十国文学于五代文学这样的层面讲,十国文学的研究还是有不少内容从未被人关注,而被关注和研究的内容又不无片面、粗浅和疏漏的缺点。由此看来,对十国文学展开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其必要性不容置疑。
二 本书的研究条件
学界涉及十国文学的研究成果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莫大的帮助,现胪述如下。
(一)早在清代前期,就有三种文史类著作将“十国”从“五代”中区分开来。
康熙八年己酉岁(1669)成书的《十国春秋》114卷(1788年周昂重刻《十国春秋》时撰有《拾遗》一卷、《备考》一卷,全书成为116卷)的编纂目的并不是为了十国文学研究,也没有《文苑传》、《文艺传》、《儒学传》之类的文人专传或学者专传来强调十国中的一些文人或学者,但是,博通经史的人鲜有不留心艺文之事者,吴任臣正是这样,他为人物作传时不仅交代传主的文艺爱好,而且常常提到传主的著作,更难得的是,行文中往往例举传主诗、词、文的名作乃至名句。这三点已经可以对十国文学研究起到辅助和促进作用了。但是,更有价值的是,《十国春秋》将五代十国时期众多的历史人物从五代中甄别出来,分置于十个不同的国家中,其中包含了十国许多文人,这就使得十国许多文人尤其是著名文人或重要文人的国别认定有了现成的参考依据。
康熙十二年癸丑岁(1673)朱彝尊所编《词综》(26卷,汪森增补10卷于1691年刊刻后成为36卷)第2卷、第3卷的题目是《五代十国词》[9],这是历史上将“十国”和“五代”并列起来作为文学资料的第一次,朱彝尊也因此成为将“十国”作为一个名词提出来以供文学研究的第一人。可是,《词综》仅限于在篇章题目上提出“十国”这个名词并将“十国”和“五代”并列(这说明在内心里,朱彝尊主张把十国从五代中分离出来),选收词的时候并没有把五代词人和十国词人区分开来,更没有把十国中的前蜀词人、后蜀词人、南唐词人、荆南词人区分开来。从事文学资料编纂时,将十国和五代区分开来,并将十国中每个国家的文人区分开来的,是乾隆四十五年庚子岁(1780)成书的《全五代诗》一书。
《全五代诗》的编者是李调元(1734—1803),全书共100卷,含五代17卷和十国83卷。五代17卷是:梁8卷、唐2卷、晋2卷、汉2卷、周3卷;十国83卷是:吴6卷、南唐16卷、前蜀17卷、后蜀4卷、南汉1卷、楚4卷、吴越9卷、闽13卷、荆南12卷、北汉1卷。尽管李调元对文人所属政权的区分不可能都正确,例如将杜荀鹤置于后梁名下、将谭用之置于北汉名下就颇值得商榷,作为历史上第一部五代十国诗歌总集,而且能把十国文人从五代文人中甄别出来、将十国中每个国家的文人区分开来,其成绩还是值得肯定的。该书一举完成了五代十国文人政权身份的认定和诗歌作品的收集这样的双重任务,其功劳不可谓不大,也使该书成为对十国文学研究最具参考价值的著作。
(二)能够成为收集十国文学作品渊薮并对《全五代诗》的疏漏起到订正作用的六种总集类著作(及其一系列订补作品),至今已经全部完成。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岁(1707),彭定求等人奉康熙皇帝之命编成了《全唐诗》900卷(卷882至卷888共7卷为《补遗》,卷889至卷900共12卷为词)此后出现了一系列补遗著作,计有:1788年日本上毛氏河世宁先生的《全唐诗逸》3卷、1936年孙望先生的《全唐诗补逸》19卷、1962年王重民先生的《补全唐诗》(不分卷,共39页)、1980年王重民先生的《补全唐诗拾遗》3卷、1980年童养年先生的《全唐诗续补遗》17卷、1988年陈尚君先生的《全唐诗续拾》60卷。以上《全唐诗》900卷及6种补遗类著作均被收入中华书局1999年1月第1版的《全唐诗》(增订本)(全15册)中。此后有零星的补遗著作出现,例如《文史》2003年第1辑(总第62辑)发表的查屏球先生《新补〈全唐诗〉102首》等。这是唐诗总集的现有成果。
20世纪30年代林大椿辑有《唐五代词》一书,80年代张璋、黄畲辑有《全唐五代词》一书,中华书局1999年12月出版了由曾昭岷、曹济平、王兆鹏、刘尊明编撰的《全唐五代词》一书,该书书名是《全唐五代词》,书中也没有将“十国”二字列入一个章节标题中,但是,其内容实际包含了十国词。所以,该书是目前收词最完备、考辨最全面的一部唐五代十国词总集类著作。
嘉庆十九年甲戌岁(1814)闰二月,董诰领衔主编的《全唐文》编成,共1000卷,收文18488篇,作者30042人,编成后即交内府刊印(全唐文将十国附五代后)。此后,光绪十四年戊子岁(1888),陆心源刊印了自辑的《唐诗拾遗》72卷,收文3000篇;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岁(1895),陆纯伯刊印了其父陆心源所辑的《唐文续拾》16卷,收文310篇。这3种著作被中华书局于1983年11月加了句点后影印出版,全12册(其中第12册为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1月出版了周绍良先生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全2册)370万余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了周绍良、赵超两位先生主编的《唐代墓志汇编续集》192万余字。中华书局2005年9月出版了陈尚君先生辑校的《全唐文补编》(全3册),共160卷,290万余字。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周绍良主编的《全唐文新编》22册,达两千余万字。这是唐文总集的现有成果。
《全宋诗》由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全宋词》(全5册),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中华书局1999年1月新1版。该书371万余字,录词人1330余家,词19900余首(不计残篇)。
《全宋文》(全360册),曾枣庄、刘琳两位先生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收作者接近1万,收文17万余篇,字数近1亿。
以上六种总集类著作,将十国文人的作品几乎全部囊括其中,这就使得十国文人诗、词、文的收集工作变得相当容易。
(三)包含了十国文学编年的唐五代文学编年类著作已经出现,对逐年考辨十国文学史实具有参考价值的正史类、载记类等多个类别的著作数量相当庞大,也比较容易找到。
1954年夏承焘所撰《唐宋词人年谱》含韦庄、冯延巳、李璟、李煜四个十国文人的年谱,在此之前,有汪德振的《罗隐年谱》、震钧的《韩承旨年谱》等几种年谱著作问世(见项目成果末尾的《引用文献》,此处略)。这些著作对十国文学编年十分有用,可称为十国文学编年的拓荒之作。以包含这些拓荒之作在内的编年类作品为基础,进行了更为深广的研究,从而成为全面系统而又相当完备的十国文学编年专著的,是辽海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由傅璇琮先生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五代卷》。《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共4册254万余字(含第四册的《人名索引》),其中第四册《五代卷》由贾晋华、傅璇琮撰写,不含《人名索引》共656页46万余字。该书对每一年的文学史实按照先中朝(即先排五代中的某一代)后十国、十国则谨遵吴任臣《十国春秋》安排(即吴、南唐、前蜀、后蜀、南汉、楚、吴越、闽、荆南、北汉)的顺序予以胪述,史实胪述之下有详细的考辨。这样的体例给读者的感觉是,五代是五代、十国是十国,全书纲举目张,脉络相当分明。该书书名虽然是《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五代卷》,但实际上是对五代文学和十国文学的编年,所以,准确点说,该书的名字应该是《唐五代十国文学编年史·五代十国卷》或《五代十国文学编年史》。再加上该书的二位作者傅璇琮先生和贾晋华先生撰写此书前曾经主编或参与撰写了《唐才子传校笺》和《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二书,故该书考辨谨严,识断精当,是研究十国文学最可靠的编年类著作。
无意于给十国文学编年提供帮助但事实上可以提供这种帮助的书数量很多,分布于多个类别。例如正史中的《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编年史中的《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载记类中的路振《九国志》、马令《南唐书》、陆游《南唐书》等;五代以来多被今人视为笔记小说的“小说类”、“杂家类”著述,例如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南宋洪迈《容斋随笔》、明杨慎《丹铅余录》、清王士祯《居易录》等。这些书籍在项目成果末尾的《引用文献》中有详细开列,此处从略。
(四)北宋以来包含诗话在内涉及十国文学评点的批评类著作,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引导。
宋佚名《后山诗话》(托名北宋陈师道)无疑是涉及十国艺文之事较早的一部诗话著作,此后谈论十国艺文之事的诗话著作数量较多,此处不予枚举。除诗话外,古人所写涉及十国文学的批评类著作亦有多种,今人所写在古代批评类著作基础上展开深广研究、成绩斐然而且对十国文学研究不无助益的著作,数量也不少。例如:罗根泽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3月新1版);罗宗强先生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9年8月第1版),等;王运熙、杨明二位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隋唐五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顾易生、蒋凡、刘明今三位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宋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等等。这些批评类著作给十国文学研究以引导,堪称十国文学研究理论方面的航标。
(五)民国以来至少在章节题目上提及或突出“十国”,或者章节题目上虽没有提及或突出“十国”但将十国囊括其中的唐五代文学研究类著作,在多个年代都有所出现。
至少在章节题目上提及或突出“十国”的唐五代文学研究类著作不算多,常见者有前文已经提到的杨荫深先生于民国时出版的《五代文学》;吴庚舜、董乃斌二位先生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五代十国文学》两章的撰写者为贺中复先生);贾晋华、傅璇琮二位先生撰写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五代卷》(辽海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张兴武先生的《五代十国文学编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将十国囊括其中的唐五代文学研究类著述,数量相当多,质量过硬者也不少,不论是数量很多的专著,还是数量更多的论文(含已发表的论文和待发表的论文,例如笔者手头有纸质文本和网络上有电子文本的学位论文),皆是这样,这些著述给予本研究成果的助益,行文中自会交代,这里就不举例了;而未能在本研究成果中出现的唐五代文学研究类著述,仍然给作者以多方面的巨大助益,这一点,必须在此特意声明并谨志谢忱。
以上五个类别的成果针对的是“十国文学研究”这样的工作,本研究的名称《十国诗文集版本考述与十国文学研究》决定了从事文献的搜集和考辨是本项目的首要任务。作为一个古籍整理和史事考辨的爱好者,笔者案头(含书架)具有从事文献工作所需要的常备工具书,例如《中国丛书综录》系列四种、《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系列、《四库全书总目》及其辨正著作系列,等等。这些书籍在行文中和项目成果末尾的《引用文献》中有详细开列,此处从略。
三 本书的研究内容
具备了文献整理、生平辨正和作品分析三方面的条件之后,依据本研究当初《申请书》的设计,需要从事如下五方面内容的研究。
第一,弄清曾经有过著作的十国文人都有哪些;这些文人各有哪些著作,这些著作的种类、流传、存佚是怎样的。这就是第一编《十国艺文志考索》。
第二,考察一下历代学者,尤其是历代刻书、藏书的学者,如何评价十国文人中有诗文集善本著作存世的文人作品。这就是第二编《十国文人集部著作序跋文字和著录文字辑录》。
第三,在辑录著录文字和序跋文字的基础上,通过比较版本异同,来弄清楚有诗文集善本著作存世的文人集部著作曾经有过哪些版本、这些版本的演变情况是怎样的、最佳版本是哪一个,并制作《流传过程和版本源流示意图》。这就是第三编《十国文人集部著作流传过程和版本源流考辨》。
第四,在收集著录文字、序跋文字以及考辨十国文人集部著作版本源流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十国文人生平事迹和作品真伪两方面有争议的问题。考察前人的争辩理由,并就此写出自己的见解。这就是第四编《十国文人生平事迹与作品真伪辨正》。
第五,通过仔细分析作品文本,并兼顾前人的选录和评价,采用以人为纲的方法,对十国文学予以尽可能全面而深入的剖析,写出一本类似于《十国文学史》的著作。这就是第五编《十国文学创作述论》。
四 本书的研究原则和方法
本书的研究尽可能遵循着这样三个原则:一是全面性原则;二是深入性原则;三是创新性原则。对这三个原则就不解释了,不解释的原因不是偷懒,而是研究开始之初就声称要遵循这三个比较动听的原则,多少有点自我吹嘘的味道,而且这种声称没有多大意义,因为谁也不会声称自己的研究遵循着片面、肤浅、抄袭的原则。不论声称遵循着什么,关键看落实得如何,毕竟说得好不等于做得好,做得好永远胜过说得好。
本书的研究方法有三个。第一是文献学的方法,指通过对材料的收集、考辨和排序,以编纂出新的文献成果。第二是逻辑学的方法,指通过比较、推理和判断,来弄清事实之真伪和事理之正误。第三是诗艺体味的方法,指通过阅读、体会和分析,去探求作家作品思想内容的广狭深浅和艺术特色的高下短长以及地位上的前之所承和后之所启,这个方面的探求永无止境而且容易见仁见智,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人完全同意,故只能说“去探求”(而不宜用“来获得”之类的措辞),但也正是因此而具有了挑战和趣味,成为本书最该严谨、最具活力、也最可能引起争议的部分。
不论是研究原则还是研究方法,预设起来都比较容易,贯彻下去都相当困难。常见的一个现象是,做事前好话说在人前,做事时承诺抛在脑后。所以,第一个需要克服的困难是,如何才能保证研究的过程中时时惦记着并且尽可能落实着五个原则和三个方法的要义。应该说,谁也不能保证、也没有任何办法能保证做到这一点,但是提出几个注意事项有助于做到这一点。以下就谈谈从事本研究的注意事项,既是给自己的研究警醒,也是给读者的阅读提示。
五 关于本书的几点说明
本着全面、深入和创新的原则,本书尽力注意如下问题:
第一,对收集到的材料一定注明出处,而且尽可能注明最早的出处,对没有收集到的材料一定说清为何没有收集到,并交代收集的线索;进行逻辑分析的时候尽可能考虑到所有的可能性,而且在自感已经考虑到并且交代了所有可能性的情况下,仍然用“其他可能”之类的用语表示自己的考虑不周,既防止自己思维可能一时短路所造成的过错,也明言请读者点拨和帮助的期待之情。这是全面性原则的一个重要体现(但不是所有的重要体现,更不是所有体现)。
第二,对前贤所使用的材料一定追溯其来源;对前贤所得出的结论一定核实其论证;发现前贤的观点正确,一定赞同,绝不敢闪烁其词或缄默不语以示治学不阿而又沉稳;发现前贤的观点有误,一定指出,并尽可能更正,绝不敢视而不见或曲为左袒以示为人谦逊而又希贤。
第三,对没有或者几乎没有研究成果的研究对象一定亲力亲为,钝锄拓荒(事实上也只好如此),对已有研究成果或者研究成果颇为可观的研究对象,在了解了已有研究成果而且没有发现任何疏漏的情况下,仍然重新研究一遍,宁愿“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对笔者自己而言,实际是第一遍苦、第一茬罪)之后一无所获,也不以尊重和善用他人劳动成果为托词,把对现有研究论著的熔铸或粉饰当作自己的收获,然后宣称“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如何如何。
第四,对使用的每一份文献材料都尽可能找到最早的出处和面目,并用前人的描述与之对比,以核实学界的成说;对需要考辨的每一个问题都尽可能罗列众说并梳理众说演变的源流,以便提出自己的观点;对分析的每一首诗都务必(注意这次不是“尽可能”了)如实地交代自己的看法,宁愿献丑以惹人耻笑,也不藏拙以守旧因循,因为学术创新的大忌(其实也是任何创新的大忌),不是众人眼里不知天高地厚的乱喷,而是自己内心对主流人物和权威说法的追随。
第五,凡遇年号纪年、干支纪年或古代其他纪年方式,一般均在其后的括号中以阿拉伯数字注出公元纪年,并省略“公元”和“年”三个字,但一般会避免一千字以内篇幅中的重复出注;凡遇人名,一般均于其后的括号内以阿拉伯数字出注生卒年份;凡遇帝王或国主,一般均于其后的括号内以阿拉伯数字加“年在位”三字出注在位年份(个别情况下的出注会精确到月份乃至日子);凡遇古书,一般均于其后的括号内以阿拉伯数字加“年成书”三字出注成书年份(个别情况下的出注会精确到成书月份,有时还注出第一种刻本的竣工时间),这些书完成和刊刻的时间一般得自于该书的序跋文字或四库馆臣所写《四库全书总目》之类的考辨文字,为免烦琐,文中对古书完成、刊刻时间的出处不再出注(确实有必要出注的情况除外)。
第六,凡笔者的解释性文字,为了使这些解释性文字得到强调而又变得醒目,不管是在括号内,还是在括号外,都以“笔者按”三字发端,但是要注意,“笔者按”三字只是为了使解释性文字得到强调并与他人的按语相区别,而不是说未加“笔者按”三字的文字,就不是笔者的话。
由于笔者的自不量力和贪多务得,本研究头绪多而内容杂,疏漏不当之处,肯定不少。诚望学界长辈和读者诸君有以教我,不胜感激。
[1] (清)李调元编,何光清点校:《全五代诗》(100卷)(全2册),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1册,目录第1—53页。
[2] 张兴武:《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4页。
[3] (清)王士禛原编,郑方坤删补,戴鸿森校点:《五代诗话》(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例言》第1—2页。
[4] 杨荫深:《五代文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页。
[5] 许总:《唐诗史》(下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12页。
[6]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30页。
[7] 杨荫深:《五代文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2页。
[8] 李定广:《唐末五代乱世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9] (清)朱彝尊、汪森编,李庆甲校点:《词综》(36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卷2—卷3,第2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