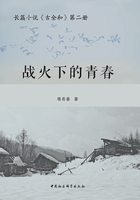
第16章
根儿吃了一些东西,又在牲口棚里睡了一觉,虽然仍然感觉浑身酸懒,但是背上的20斤小米儿,并没让他感觉多么沉重。最让他高兴的是他爹就在他的身边,他不必为他爹的安危提心吊胆。想到自己能替大人分忧心里有说不出的得意。但是他轻松的时间并不长。身上的热气儿很快消散,严寒从四面八方袭来。根儿感觉吸进鼻子里的好像不是空气,而是数不清的细细的钢针,呼吸变成了一种他必须小心承受的痛苦。走了一阵子后,他感到背上的米袋子也开始变得沉重起来。
一切都融化在黑暗里。谁也看不见谁。没有人说话。人们脚踏积雪的嘎吱声,因为负重和不时的奔跑而发出的粗重的喘息声,和由于汗湿和冷冻而变得僵硬的衣服自相摩擦发出的沙沙声……所有的这些声音都显得出奇地大,好像从很远的地儿就能听见,在周围死一样的寂静里而显得特别可怕,加重了他们内心的恐惧。
赵凤山走在最前面。孩子们被夹在大人中间。根儿紧跟在他爹的身边。大家一会儿爬上高坡,一会儿又走进低地。不时有人跌倒,又在同伴儿的拉扯下爬起来,人们的呼吸声越来越响,心情也越来越紧张。
“小心!前面是高粱地!”赵凤山警告道。
赵凤山的提醒,让胡大珂紧张起来。他知道,这里收秋的习惯和山东家不一样。在山东家,吃的和烧的都十分珍贵,粮食要颗粒归仓,庄稼的秸秆儿也要尽可能地收拾回家。收高粱的办法儿是先把高粱穗子一个个地用特制的锋利的刀子割下来,捆扎成一个个方方正正的高粱头运回家,然后用三尺手镐把高粱秸一棵一棵地从地里刨出来,打掉根儿上的泥土,运回家贮藏起来,用作烧柴和手工编织的材料。而本地人做饭取暖有木柴和煤炭,人们并不特别珍惜高粱秸。他们收高粱的办法是用镰刀把高粱从离地一尺多高的地方斜抹茬着削下,留在地里的那些近一尺高的高粱楂子,像支支利剑成行地竖立在一条条垄背儿上,有谁不小心摔倒,坐上去,就会被刺伤,如果刚好刺中要害地方,比如说扎进肛门或是其他要紧的部位,会有生命危险。胡大珂想到这些,就攥紧根儿的手,一刻也不敢放松,几乎是提着他在高粱地里的垄间朝前奔走,不时悄声儿提醒他说:“不要慌!小心!别摔倒!”
惊恐和紧张使根儿忘记了寒冷,但是他仍然觉得背上的米袋子越来越重,挂在两肩上的两根“高丽背”上的绳子像是要杀进肉里,腿又好像不是他自己的了,挪动脚步开始有些困难,身子也总是摇摇摆摆,一脚深,一脚浅,把握不住方向和平衡。这时他才明白他爹说的“远路无轻载”是什么意思,他爹为什么不准他和道士和素桂一样,也背25斤小米儿了。根儿知道到前面的路还长,说不定还会碰上警察,但是他不后悔。他觉得,就是像现在这样受苦受累,也比在家里整宿整宿地为爹担惊受怕要好受些。
“还行吗?”素桂问他。
“行!”他不愿意让人觉得他不行,尤其是素桂。
远处传来了犬吠声。有人说那是警犬的叫声。
“趴下!”赵凤山命令道。
根儿急忙趴在地上,猜想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的心怦怦地跳起来,强烈地震动着他的耳鼓。他尽力屏住呼吸,生怕被人听见。他突然觉得这里好像只有他一个人。他觉得孤独,想家,想古家庄那个家。就连“鬼屋”里的那个家他都觉得亲切,那里有奶奶和娘。
几道手电的光柱儿从远处朝他们这里扫来扫去。
“出来吧,你们跑不了啦!”远处有人高声喊叫。
“老一套!”赵凤山气愤地说。
“再不出来我们可要放狗啦!”一个年轻的声音。
周围死一样地静。即使碰响一片地上干枯的高粱叶子,那声音也像雷鸣,让人心惊。
“不理他们,他们在诈咱呢!”赵凤山严厉地提醒道。
手电光终于熄灭了,喊声也停止了。赵凤山知道,在日本人眼里狼狗比满洲警察的命更值钱,担心狼狗再次被他们打死打伤,不会轻易放狗。
赵凤山没有命令大家起来。他知道警察仍然在附近盯着他们,他要等警察耐不住寒冷而离开这里以后再动身。他相信,虽然警察吃的是大米白面、鸡鸭鱼肉,有皮鞋、皮帽和皮大衣,可是他们仍然扛不过他们这些不要命的人。
根儿觉得浑身冰凉,汗水把衣裳紧紧地粘在身上。
随着一阵窸窣声,一只大手停在他的身上。根儿知道,这是他爹的手。他顿时觉得周围温暖了许多,孤独的感觉消逝了。胡大珂摸索着卸下根儿背上的粮食,让他站起来轻轻地活动活动身子。根儿感到从没有过的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