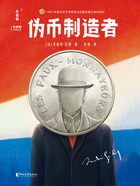
导读
在“伪币”的世界中追寻本真
以“故事”之名
在《伪币制造者》的扉页上,纪德留下了这样一段题词:
我把自己的第一本小说献给罗杰·马丁·杜·加尔,以此见证我们深厚的友谊。
纪德把1925年出版的《伪币制造者》称为自己的第一部“小说”(roman)。在此之前,他已经发表过《背德者》《窄门》《田园交响曲》《梵蒂冈地窖》等多部重量级作品。作为一位著作等身的大作家,在年近六旬时出版自己的第一部“小说”,这显然非同寻常,说明纪德本人对于“小说”自有一套独特的界定标准。事实上,纪德关于“小说”的看法确实与众不同,他把自己之前写下的那些作品统统称为“récit”,可以理解为“叙述、故事”,而“roman”唯有《伪币制造者》一部而已,其区分标准显然不是作品篇幅的长短。在一份为《伊莎贝拉》注1准备的前言草稿中,纪德曾经这样写道:
为什么我特地把这本小书称为“故事”呢?单纯是因为它没有回应我对于小说的看法,《窄门》或者《背德者》也没有,而我不想大家混淆。小说,按照我的理解或者构想,包含着观点的多样性,服从于出场角色的多样性,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分散的作品。
在纪德眼中,小说应该是一种分散的、复调的、包含各类不同观点的作品。这在《伪币制造者》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从小说的情节设置来说,在四十多个章节中,叙述视角发生了多次变更,有贝尔纳的角度,有奥利维耶的角度,有爱德华的角度,还有文森、劳拉、莉莉安、拉佩鲁斯、阿扎伊斯、莫利尼耶、坡菲唐迪厄、帕萨凡等人的角度。同样一件事,每个人看到的内容、产生的观点都不尽相同,他们各自获得的认知也许并不符合事实,于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碰撞,呈现出一种众声喧哗的整体效果,使得小说中的每一位过场人物都具有相对饱满的形象乃至于独立完整的故事。借助高超的技巧,纪德编织出一张精美的叙事之网,各种人物的淡入淡出都显得恰到好处。与此同时,纪德在作品中特意设置了作家爱德华的角色,他正在酝酿一部同样题名为《伪币制造者》的小说,于是他的诸多想法便很自然地与整部作品形成了呼应:
你们要理解我,我想要写的东西类似于《赋格的艺术》。我不明白为什么音乐中可行的东西到了文学里面就做不到……
《赋格的艺术》是德国著名作曲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最后的音乐作品,对复调音乐的对位法进行了极其深入的探索,在一个单一主题及其对位法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复调音乐的创作。复调和对位,构成了《赋格的艺术》的基础。而爱德华对于自己那本小说的构想,在纪德本人的作品中得到了实现:贝尔纳离家出走——劳拉有家不回——文森逃入林莽;贝尔纳与爱德华的瑞士之旅——奥利维耶与帕萨凡的科西嘉之行;贝尔纳对劳拉的精神之爱以及对莎拉的肉体之爱;爱德华先后四次探望拉佩鲁斯;还有小说中涉及的好几对夫妻、父子关系,这些都是同一主题的多声部对位。
小说以一种碎片化的方式来书写整体,借助一个个片段串联起完整的故事,多条线索在同一时间展开,有如电影画面般不断切换,最后综合各人的视角呈现众生百态。爱德华认为小说不能再像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那样去跟“户籍”竞争,认为不能像自然主义者那样单纯从时间的长度方向对人生进行切片。这些关于小说创作的“元叙事”,都在纪德的创作中得到了实践。
事实上,整部《伪币制造者》中,对于文学本身的描述同样构成一重复调:爱德华的态度、帕萨凡的态度、斯特鲁维乌的态度、阿尔芒的态度、索弗洛妮丝卡的态度等。从中读者一方面可以发现法国文学史发展的某些现实脉络——比如二十世纪初达达主义的嘲讽与破坏欲,另一方面也可觉察到作者所营造的一种独特的知性空间,在小说中思考、陈述、辨析小说的价值,把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有机结合,并与整部作品形成隐性对照。
“伪币”的多面一体
下面来谈谈内容。小说的原标题:“Les Faux-monnayeurs”,在法语里带有复数“s”。换言之,小说中涉及的不是一位“伪币制造者”,而是一群:制售假币的斯特鲁维乌,借一群年轻学生之手拿假币换取财货,破坏商业与社会秩序,这是制造伪币的基本含义,意味着经济交流基础的崩坏。罗贝尔·德·帕萨凡这种拾人牙慧的假文人(“Passavant”这个名字,在法语中可以理解成“pas savant”,即“没有学问、不学无术”),沉迷于趋附时尚、蝇营狗苟。他也在制造伪币,令文学变得矫揉造作,无法直击人心,导致文学丧失沟通和交流的能力,变成了一种包装精美的赝品。他隐于幕后,雇佣斯特鲁维乌代替奥利维耶出任杂志主编,使得这种双重作伪在暗中形成了合流。
以上这两种“伪币制造”,属于较为具象的层面。更进一步的,是某种道德层面的伪币。例如文森,他对劳拉摇摆不定的责任感背后,蕴藏着一种道德压力导致的迫不得已。而他在结识格里菲斯夫人之后,后者带给他一种更加“背德”的生活态度,就像她讲述的那段关于海难与砍手的经历一样,促使他斩断了自己与劳拉的联系,并从阿尔芒的哥哥亚历山大的来信中透露出他最终结果了格里菲斯夫人,整个人也随之陷入了迷狂。
此外,还有情感方面的伪币、人性方面的伪币。比如小说中出现的几对夫妻:面对贝尔纳私生子身份曝光后的离家出走,坡菲唐迪厄先生希望将情绪从痛苦引向救赎,曾经出轨的坡菲唐迪厄太太关心的却只是“他是怎么发现的呢?是谁跟他说的呢?”随后一走了之,毫无悔意,他们之间的交流是失效的;拈花惹草的奥斯卡·莫利尼耶在听天由命的宝琳娜面前百般遮掩、得过且过,心里记挂的只有那些偷情信件的下落,他们之间的交流也是失效的;拉佩鲁斯老爹跟他的太太完全是鸡同鸭讲,两人生活在无休止的相互指责之中,他们之间的交流同样是失效的。这些统统是伪币。至于盖里达尼索尔在学校里组织的强者协会,以友情为诱饵霸凌小鲍里斯,最终导致鲍里斯被害身亡,盖里达尼索尔却借助自己的少年身份逃脱了重罪处罚,这当然也是伪币。
这些各种各样的“伪币”可以引出多种多样的阐释。比如从社会学的角度可以说,纪德从这个生活切面写出了时代的虚伪与传统价值的崩解,影射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社会的动荡不安。但笔者想在这里强调的,还是回归人与人之间的状态本身。比如爱德华与奥利维耶,他们互相欣赏:爱德华特意在寄给奥利维耶父母的明信片中标明自己回程的班次,期待奥利维耶能够发现这个隐藏线索;奥利维耶心心念念去火车站迎候,在前天夜里对贝尔纳大谈特谈,幻想向爱德华求取文学与人生的指导。但当他们在火车站碰面之后,互相给对方留下的印象却全是误解:
但是爱德华最浅淡的微笑便令他心伤,要不是担心表情会显得过于夸张,他就会透露出那些令其心神不宁的躁动情绪。他沉默不语,感到自己板着脸,真想投入爱德华怀中哭上一场。爱德华却误会了这种沉默,误会了这张苦脸上的表情。他太喜欢奥利维耶了,以至于完全失了从容。如果他敢看奥利维耶一眼,他就会把对方抱在怀里,像对待孩子一样加以呵护。当他与对方沮丧的目光相遇时: “就是这样,”他心想,“我令他厌烦……令他疲倦困乏。可怜的小家伙!他就等我一句话以便脱身。”而这句话,出于怜悯,爱德华不由自主地说了出来: “现在你该走了。你父母在等你吃中饭呢,我敢肯定。” 奥利维耶也有同样的想法,这下轮到他误会了。他赶紧站起身,伸出手掌。最起码他想对爱德华说:“我什么时候能再见你呢?”“我什么时候能再见您呢?”或是“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呢?”爱德华等着这句话,但听到的却只是一句平淡的“告辞”。
在这一句平淡的“告辞”中,纪德写出了一种深深的孤独感,一种近乎命运的隔阂。两个心系对方的人,为什么却收获了这样悲凉的结果?这恐怕比斯特鲁维乌或者帕萨凡的“伪币”更加令人心痛。但这恰恰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伪币:如果说寻常的伪币是在玻璃上镀金,让人误以为是真金币,那这种伪币就是在金上镀玻璃,让人误以为只是廉价的玻璃。这种伪币不仅仅存在于奥利维耶与爱德华之间,还包括鲍里斯和拉佩鲁斯老爹之间,拉谢尔和她的父母之间……宝琳娜、劳拉、坡菲唐迪厄……小说里的一个个人物都在生命中的某些时刻遭遇过这种伪币。如何应对?办法当然是求真,或者说让真金从玻璃之下透露出来。就像奥利维耶在自杀未遂之后,终于向爱德华袒露心扉;坡菲唐迪厄在爱德华面前坦承自己对贝尔纳的关爱,最终促使贝尔纳回到家中。爱德华在日记中描述了这打动人心的一幕:
“主啊!”他又补充了几句,“千万别和他说这事儿!他的性子那么骄傲,那么多疑!……要是他感觉到,自从他出走之后,我就不断地想着他、盯着他……不过您还是可以告诉他,您见到我了。(他每说完一句话都要费力地喘口气。)——只有您一个人可以跟他说的内容,就是我不怨他,(随后用更微弱的声音说道)说我从来没有停止爱他……像儿子一样。是的,我完全清楚您了解内情……您还可以对他说……(他的眼神没有看着我,在一种极度困窘的状态下艰难地说道)他母亲已经离开我了……是的,今年夏天一去不返了。如果他愿意回来的话,我……” 他没能把话说完。 一个魁梧健壮、积极向上、在人生中颇有建树、事业有成的男子,突然抛下全部礼节,在一个外人面前敞开心扉,真情流露,让我这个当事人看到了无比震撼的一幕。趁此机会,我得以再次确认,相比熟人的一诉衷肠,我更容易被陌生人的肺腑之言打动。改天我会争取把这一点解释清楚。
坡菲唐迪厄在爱德华面前关于贝尔纳的一番自白,说出了他本人在贝尔纳面前也许永远不会说出的话。所以爱德华的评述也许可以反过来看:为什么人们可以在外人面前敞开心扉,真情流露,却很难对熟人一诉衷肠呢?这种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或者泛言之,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无疑也是纪德着力描写的伪币之一。
在日记中,爱德华曾经提到一句《福音书》中的“绝妙箴言”:“如果盐失去了它的味道,用什么让它恢复咸味呢?”表面上看,无论爱德华还是纪德似乎都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但如果换一种表述,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如何在充斥着伪币的世界中寻找本真?这可以被视为小说中一系列剧情的核心。我们甚至可以问:文森在寻找本真吗?他斩断萍水相逢的恋情离开劳拉,背弃了父母家人的期许放弃医学,如何理解他的行为?阿尔芒用嘲弄的方式摧毁他珍视的一切,如何判断他的立场?出走的贝尔纳可以归家,犯错的乔治可以扑进母亲怀中,但离世的鲍里斯却永远无法在拉佩鲁斯老爹怀中醒来。纪德并没有给出一劳永逸的答案,小说中的一个个人物,都像是多声部的探索,用他们各自的经历,展现某种可能。而这也许就是纪德的教导:
只有经历生活,才能学会应该如何生活。
张将
2023年10月
注1 《伊莎贝拉》:纪德所著小说,于191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