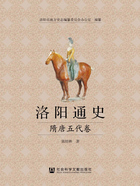
第一节 隋代洛阳的宗教
一 隋文帝时期洛阳佛教的复兴
南北朝后期,北朝的北齐、北周两个政权处在东西对峙的状态。北周境内有佛寺一万所,僧尼近一百万人,对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军事实力造成严重的影响,周武帝决心“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1]建德三年(574),他下诏毁佛,没收寺院及其田庄,销毁铜像、佛经,勒令僧尼还俗,编入民籍。三年后北周灭掉北齐,将那里的三万所寺院财产全部没收,两百万僧尼被勒令还俗。大象二年(580)五月,周宣帝病故,杨坚辅佐儿童皇帝周静帝,总揽全国大权,于六月宣布:“复行佛、道二教。旧沙门、道士精诚自守者,简令入道。”[2]开皇元年(581),杨坚建立隋朝,开始正规复兴佛教。隋文帝诏令全国,听任民众出家为僧,并按人口摊派缴纳钱币,用于营造佛像、抄写佛经。京师长安和洛州等重要地区,皆由官方组织抄写佛经,置于佛寺和秘阁中。民间佛经数量比儒家六经多出数十百倍。开皇四年(584),关中大旱,隋文帝带领百官和一部分民众转移到洛州解决吃饭问题,邀请京师长安大兴善寺律僧灵藏同行。洛州民众纷至沓来,归投灵藏。隋文帝对灵藏说:“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师为道人天子。有乐离俗者,任师度之。”灵藏“遂依而度,前后数万”。[3]开皇十一年(591),隋文帝“诏州县各立僧尼二寺”。[4]洛州及其所辖县贯彻诏令,集资造寺。
仁寿元年(601)、二年(602)、四年,隋文帝诏令分送所谓释迦牟尼的舍利于一百余州,于四月初八佛诞节入函立塔。建塔的经费,由民众施舍。僧人灵幹曾负责护送舍利,从大兴城来洛州建造舍利塔。僧人宝袭曾负责来洛州嵩山嵩岳寺建造舍利塔。时人王劭《舍利感应记别录》记录仁寿二年(602)的情况,说:“洛州表云:舍利三月十六日至州,即于汉王寺内安置。……四月七日夜……在佛堂东南,神光照烛,复有香风而来。……至八日临下舍利,塔侧桐树枝叶低茎。”[5]
开皇七年(587),隋文帝从各地征聘几位高僧入京师长安,研究、传播佛教经典。其中有慧远,俗姓李。北周毁佛时,他被迫还俗,躲藏起来诵读佛经。周宣帝时,他被选中作为菩萨僧,安置在洛阳陟岵寺(嵩山少林寺)研究佛学。隋文帝执政之初,他再度出家,与一批道友相约来到洛阳,弘扬佛法,远近僧人得知消息,纷纷前来参学请教。隋文帝任命他担任洛州沙门都。他贯彻戒律教规,严格整饬僧众。僧人或不漉水护净,或乞食违背教规,或威仪失常,一律清除出去。其余懒惰贪睡,听讲迟到,都加以惩处。一时间“徒侣肃穆,容止可观”。开皇七年(587),他受诏赴京师,五年后在长安净影寺去世。同时大臣李德林也去世了,隋文帝感叹道:“国失二宝也。”[6]慧远一生四处讲经,对于重要的经典还撰写了注疏,计有五十余卷,在各地流行。
二 隋炀帝设立东都内慧日道场
隋炀帝杨广早年任扬州总管期间,奉佛教天台宗创始人智 为师,请他为自己授菩萨戒,成为菩萨戒居士,法名“总持”。开皇十九年(599),杨广在扬州设立慧日、法云两个佛教道场,邀请学问僧、律僧在其中研究、弘扬佛教,自己的晋王府出资供养。杨广被立为太子后,扬州佛教道场的一批僧人被他带到首都长安,安置在自己所立的日严寺中。杨广称帝后,在东都洛阳设立内慧日道场,该道场成为皇家佛教研究院,他又把这批僧人中在世者带到东都,安置在内慧日道场中。
为师,请他为自己授菩萨戒,成为菩萨戒居士,法名“总持”。开皇十九年(599),杨广在扬州设立慧日、法云两个佛教道场,邀请学问僧、律僧在其中研究、弘扬佛教,自己的晋王府出资供养。杨广被立为太子后,扬州佛教道场的一批僧人被他带到首都长安,安置在自己所立的日严寺中。杨广称帝后,在东都洛阳设立内慧日道场,该道场成为皇家佛教研究院,他又把这批僧人中在世者带到东都,安置在内慧日道场中。
据《续高僧传》记载,隋炀帝带到东都内慧日道场中的僧人,都是南方僧人。智脱是江都郡人,法澄是吴郡(治今江苏苏州市)人,道庄是扬州建业(今江苏南京市)人,法论是南郡(治今湖北江陵市)人,立身是金陵(今江苏南京市)人,智果是会稽剡县(今浙江嵊州市)人。同时,隋炀帝还在全国范围内选拔杰出僧人,充实到东都内慧日道场中。敬脱是汲郡人,辩相是瀛州(治今河北河间市)人,法护是赵郡(治今河北赵县)人,智徽是泽州高平(今山西高平市)人,法安是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县)人,道基是东平(今山东郓城县)人,志宽是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市)人。此外,还有景法师、严法师。这批杰出的僧人,精通佛教经论,不但经常讲解各派经论,还有注疏著述,有的还广泛涉猎道家、儒家著作,通晓经史文学、语言文字学,擅长书法。有的还在东都鸿胪寺给来华的外国僧人授课。
东都内慧日道场的设立,体现出隋炀帝的学术追求。在南北朝分裂时期,南北佛教,风格异趣,南方重理论,北方重实践,即所谓南义北禅。伴随着隋朝的政治统一,南北佛教风格也应该统一,于是天台宗提出了定慧双修的止观法门。止即禅定,属于佛教实践;观即智慧,属于佛教理论。
印度小乘佛教时期,把佛教归纳为戒、定、慧“三学”。戒是学佛者的入手法门,目的在于纯洁身心、防范过失。定即禅定,是打坐静默活动,以此调练心意,专注于一境,产生佛教智慧,正确观悟人生,成就各种功德。慧是区别于世俗认识的智慧,能通达诸法性空的真理,根绝迷妄,因而是诸佛之母。三学的关系是:慧是根本,戒、定是方便(灵活手段)。依止于戒,心乃得定,依止于定,智慧乃生。和三学对立的贪、嗔、痴是“三毒”。贪,指贪爱、贪欲;嗔,指仇恨和损害他人的心理;痴,指不符合佛教智慧的愚痴无明状态。佛教倡导以戒破贪,以定破嗔,以慧破痴,这便是“立三学,破三毒”。由于戒是入手法门,最基本的戒规,出家佛教徒和在家佛教徒都要奉行、遵守,所以戒是自不待言的要求,可以略去不提,那么,便剩下定和慧了。智 主张定慧双修,实际上包含了戒、定、慧三学全部。他认为禅定和智慧,二者密不可分,就好像车子的两个轮子、鸟的两只翅膀,如果缺少一个轮子,车子就难以行驶、停留,如果缺少一只翅膀,鸟就不能飞翔。所以仅仅停留在禅定层面上,不考虑用佛教思维去产生精神活动,观悟宇宙、人生,那叫作“愚”;仅仅依据佛教思维去产生智慧,不从事禅定活动,便得不到种种福德,那叫作“狂”。
主张定慧双修,实际上包含了戒、定、慧三学全部。他认为禅定和智慧,二者密不可分,就好像车子的两个轮子、鸟的两只翅膀,如果缺少一个轮子,车子就难以行驶、停留,如果缺少一只翅膀,鸟就不能飞翔。所以仅仅停留在禅定层面上,不考虑用佛教思维去产生精神活动,观悟宇宙、人生,那叫作“愚”;仅仅依据佛教思维去产生智慧,不从事禅定活动,便得不到种种福德,那叫作“狂”。
北方佛教重禅定,早已形成传统。南天竺僧菩提达摩来华,先到建康(今江苏南京市),和梁武帝交谈,机缘不契,遂于北魏正光元年(520)来嵩山少林寺,从事禅观实践,从学者甚众。他面壁结跏趺坐,终日默然,长达九年,因而有壁观婆罗门之称。当时,洛阳禅僧还编造神话,以推波助澜。洛阳崇真寺僧慧嶷死后七日复活,说阎罗王复审新近死掉的僧人,自己被错招到阴间,因而放回阳间继续生存;两位僧人生前分别以坐禅、诵经为业,都被安排升入天堂;另外三位僧人生前分别讲经、造经像、造寺,都被打入地狱。执政的灵太后顺从这种导向,在宫廷内供养百名禅僧,下令禁止僧人持经像乞讨。“自此以后,京邑(洛阳)比丘皆事禅诵,不复以讲经为意。”[7]
隋炀帝拜智 为师,受到天台宗的濡染。隋炀帝长期居住在扬州,对南方佛教重视理论研究有相当的了解,所以在扬州设立佛教道场,组织义学僧人开展佛学理论研究。他之所以在洛阳设立内道场,是以南方佛教改造北方佛教,消泯二者的差异,融汇为统一风格。灌顶是智
为师,受到天台宗的濡染。隋炀帝长期居住在扬州,对南方佛教重视理论研究有相当的了解,所以在扬州设立佛教道场,组织义学僧人开展佛学理论研究。他之所以在洛阳设立内道场,是以南方佛教改造北方佛教,消泯二者的差异,融汇为统一风格。灌顶是智 的徒弟和接班人,被尊为天台宗五祖。仁寿二年(602),杨广以太子身份在长安下令说:“近令慧日道场庄、论二师讲《净名经》(《维摩诘所说经》),全用智者(智
的徒弟和接班人,被尊为天台宗五祖。仁寿二年(602),杨广以太子身份在长安下令说:“近令慧日道场庄、论二师讲《净名经》(《维摩诘所说经》),全用智者(智 )义疏判释经文。禅师(灌顶)既是大师高足,法门委寄,令遣延屈,必希霈然并《法华经疏》随使入京也。”[8]庄、论二师即道庄、法论二僧。杨广当时把他们从扬州慧日道场请到长安日严寺,与灌顶一起,依照智
)义疏判释经文。禅师(灌顶)既是大师高足,法门委寄,令遣延屈,必希霈然并《法华经疏》随使入京也。”[8]庄、论二师即道庄、法论二僧。杨广当时把他们从扬州慧日道场请到长安日严寺,与灌顶一起,依照智 的注解来讲解佛经。道庄、法论后来被安排到洛阳内慧日道场中,依然承担着以南方佛教义理来补充和完善北方佛教禅观的任务。
的注解来讲解佛经。道庄、法论后来被安排到洛阳内慧日道场中,依然承担着以南方佛教义理来补充和完善北方佛教禅观的任务。
三 隋炀帝设立东都上林园翻经馆
隋炀帝设立东都洛阳内道场,旨在就已经翻译过来的佛教典籍进行研究、教学、传播、弘扬。为了进一步拓展佛教领域,别开生面,还需要将那些没有翻译过来的重要佛教典籍翻译成汉文。于是大业二年(606),隋炀帝在东都上林园设立翻经馆,其中的僧人叫作学士。隋朝的译经中心从长安转移到了洛阳。
上林园翻经馆在城区东隅,南临洛河。翻经馆内有十多个外国僧人。南天竺僧达摩笈多,开皇时期来长安,在大兴善寺翻译佛经。上林园翻经馆建立之际,隋炀帝立即征聘他以及诸学士来这里从事翻译。他在这里工作了十四年,直到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去世,连同他在长安的工作,共翻译经论七部,合三十二卷。翻经馆中的中国僧人,最突出的是彦琮。彦琮询问达摩笈多所游历的国家和地区,多是前史不曾记载的,于是撰成《大隋西国传》一书,共十篇:一方物,二时候,三居处,四国政,五学教,六礼仪,七饮食,八服章,九宝货,十山河、国邑、人物,“斯即五天(东西南北中五天竺)之良史,亦乃三圣之宏图”。[9]
彦琮精通汉文和梵文,其译经活动起步于长安。上林园翻经馆建立后,他被安排担任主事。这时,隋朝平定了林邑,获得贝叶经五百六十四夹,合一千三百五十余部,隋炀帝下诏送入翻经馆,交付彦琮披览,编叙目录,次第翻译。彦琮撰成五卷目录,分为经、律、赞、论、方字、杂书等类,估计译成汉文,应有二千二百多卷。他前后译经共二十三部一百余卷,卷首制序叙事。大业六年(610)七月,他在翻经馆中病逝。彦琮哥哥的儿子僧行矩,从小便追随彦琮,请益佛经,参与长安、洛阳两馆的翻译活动。翻经馆还是一所外国语学校。彦琮在这里向达摩笈多学习梵文,行矩、智通等僧也在这里学习梵文。智通“往洛京翻经馆学梵书并语,晓然明解”,入唐后参与翻译佛经,“善其梵字,复究华言,敌对相翻,时皆推伏”。[10]
彦琮通过长期的翻译实践,形成了深切的体会,于是写成《辩正论》,提出系统的翻译理论。《辩正论》指出,十六国时期的释道安说过,将外文佛经译成汉文,有“五失本三不易”。“五失本”指翻译佛教典籍,有五种失却外文原典本真面目的现象。其一,汉文和外文遣词造句的顺序颠倒,将外文佛经译成汉文,只能遵循汉语的规范,将其前后倒置过来。其二,外文佛经朴实无华,而汉人讲究文采,译文文采斑斓才传得开,这便在行文风格上出现差异。其三,外文佛经内容重复烦琐,反复叮咛,用散文说说,又用韵文说说,汉文译文需加以精简剪裁,撮取大意,另铸文字。其四,外文佛经结束语,用很大的篇幅归纳该典籍的大意,与前文的字句重复,翻译成汉文时皆需删除。其五,外文佛经结束一个意思,过渡到另一层意思时,又把前面说过的话再倒腾出来说说,汉文译文必须全部删掉。“三不易”指翻译佛教典籍,有三方面的艰难情况。其一,佛经是释迦牟尼佛在遥远的年代针对当时的情况所做的教诲,时代推移,情况变化,汉文译文要删除一部分往古的内容,才能让今天的读者接受,斟酌起来,颇费周折。其二,圣贤和凡夫,差别很大,要把远古圣贤的微言大义,译得使今天的芸芸众生都能读懂,实在太艰辛了。其三,阿难、迦叶(摄)等天竺高僧,都是佛陀杰出的弟子,经佛陀耳提面命,对佛经的含义尚且需反复推敲,才能求得正解。而今过了千余年,僧众的水平又远远低于那些弟子,要译得符合原意,真是难乎其难。
彦琮针对道安指出的这些情况,提出两方面意见。一方面,他主张学习梵文,直接读佛教典籍原本,以避免汉文译文走样带来的理解偏差。但佛经既有梵文本,又有其余文字的胡本,中国人有几个能直接读原本?因而这个建议不具备可操作性。另一方面,他对翻译提出“十条八备”说。“十条”指字声、句韵、问答、名义、经论、歌颂、咒功、品题、专业、异本,说的是翻译技术问题和文体分类。“八备”指的是译者的整体素质。其一,译者对待佛教,信仰要虔诚,要发愿解救众生,不要害怕耗费时日。其二,译者应以戒律规范自己的言行,道德品质高尚,有好名声。其三,译者应精通所有佛教著作。其四,译者应通晓各种世俗学问,擅长写作。其五,译者应气度轩昂,没有意必固我的坏毛病。其六,译者应淡泊名利,潜心钻研佛教。其七,译者应具有梵文修养,懂得怎样译成汉文。其八,译者应经常阅读《三苍》《尔雅》之类的语言文字书籍,懂得真草隶篆各种字体,能熟练驾驭语言文字。这八点,包括宗教态度、职业道德、知识结构、学品学风、翻译能力等方面,他认为都具备了,才是合格的翻译家。这些说法,应该是翻译工作的不刊之论。但道安提出的那些问题,彦琮的提案并不能加以解决,比如中外文的语序问题,两者的繁简、质文问题,这是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语言文字、学风文风和审美取向的问题,只要差异存在,就不能强求照搬。
四 隋代龙门石窟、佛寺和僧人
洛阳市区南的龙门石窟,原称伊阙石窟。伊河在这里自南向北流去,河东是香山,河西是龙门山,远望像阙楼。太和十八年(494),北魏迁都洛阳,承袭当年在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开凿云冈石窟的余风,开始在伊阙开凿石窟。仁寿四年(604),隋炀帝登上邙山南望伊阙,说:“此非龙门耶?”[11]伊阙石窟因而又称为龙门石窟。现在确认的隋代纪年造像只有三处。第一处是开皇十五年(595)裴慈明在宾阳南洞外北侧所造的一铺阿弥陀佛像龛。第二处是大业十二年(616)蜀郡成都县募人李子斌在宾阳中洞北侧所造的一铺观音龛。第三处是大业十二年河南郡兴泰县(今河南伊川县)人梁佩仁在宾阳南洞北壁所造的释迦牟尼佛、二菩萨双龛,竣工于该年七月十五日,这一天是佛教节日盂兰盆会,是民间超度死者的节日。梁佩仁的儿子死了,父亲为儿子做功德,出钱雇人雕造了这铺像龛。“造像龛为两个相邻的尖拱龛,内造一佛二菩萨。左龛像头残,胸隆,身着下垂袈裟,结跏趺坐于方形台座上,左手抚足,右手上举,残。台座中间是香炉,两侧各配以狮子。二菩萨头戴高莲花宝冠,头上宝缯直下至底座,面相饱满,双手合十,衣饰不清,头光火焰宝珠形。右龛造像基本同左龛。两龛中间是大业十二年造像碑,蟠龙碑头。造像记为六行,每行十一字。该龛造像虽也丰满圆润,但在艺术上还不够成熟,是从北魏向唐代过渡阶段的代表作。”[12]

图2-1 龙门石窟宾阳南洞北壁隋梁佩仁造像龛
隋代洛阳城和洛州地区有很多佛寺,著名的有少林寺和净土寺。
少林寺位于今河南登封市西北嵩山山脉的少室山麓,始建于北魏迁都洛阳的第二年,即太和十九年(495),是北魏孝文帝为安置天竺僧人跋陀而建造的,少室山麓周围林木葱茏,故兼取少林二字为名。少林寺是禅宗的祖庭。禅宗东土初祖菩提达摩即入住少林寺,从事禅观实践。相当长的时期内,嵩山地区保持着菩提达摩渐悟法门的门风,具有不能被别的地方取代的地位。
周武帝毁佛时,少林寺僧众还俗,各奔东西。周宣帝继位后,于大象元年(579)在长安、洛阳各立一所陟岵寺,少林寺被选中作为洛阳的陟岵寺。隋文帝杨坚当时辅佐朝政,从还俗僧人中挑选出一百二十人,令其蓄发不剃,穿着俗人衣服,充当菩萨僧,分配到长安、洛阳的陟岵寺中。慧远法师、洪遵律师、灵幹等人,被分配到洛阳陟岵寺中。隋文帝登基后,从全国范围内前后两次挑选十大德和六位高僧进长安翻译佛经、研究佛教,慧远、洪遵都在其选。“陟岵”的含义是儿子纪念父亲,陟岵寺的命名,意味着周宣帝为先父周武帝做功德。隋文帝建立隋朝后,陟岵寺的名字便显得不妥了,于是恢复了少林寺的原名,并把寺西北五十里处柏古山庄的一百顷土地赐给少林寺。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少林寺建筑被焚毁,只有灵塔巍然独存。
隋代净土寺在洛阳东城墙的中门建阳门(唐初改称为建春门)内,在洛河以南。玄奘法师少年时,被二哥长捷法师带到这所寺院中糊口度日。长捷天天为弟弟讲解佛教义理,并教他很多世俗学问。大业八年(612),隋炀帝下诏在洛阳剃度十四人为僧。佛学优秀者数百人前来应选,玄奘年仅十三岁,被破格以沙弥身份录入僧籍。主持这项工作的大理卿郑善果对同僚们说:“诵业易成,风骨难得。若度此子,必为释门伟器。”[13]玄奘从此在净土寺中出家。
僧人灵幹在周武帝毁佛运动中还俗。杨坚掌控北周朝政时,灵幹被选拔为菩萨僧,安置在洛阳陟岵寺中。杨坚建立隋朝后,灵幹于开皇三年(583)在净土寺重新剃度。洛阳人孟暠的儿子中有三个当了僧人,法名分别是明旷、道岳、明略。明旷十七岁出家,对于佛教理论、戒律有透彻的研究,“学徒百数,禅观著绩,物务所高,即洛阳净土寺明旷法师是也”。[14]
僧人慧乘原是隋炀帝当晋王时扬州慧日道场的家僧,大业六年(610),他奉隋炀帝诏命,作为三大德之一来东都,在四方馆仁王行道。隋炀帝任命他为大讲主,他接连三天三夜讲论佛教,条分缕析,酣畅淋漓,赢得听众阵阵喝彩。两年后,隋炀帝在东都,安排在长安为已故的父母建造两座七层木塔,派慧乘从东都送去舍利,埋在塔下。大业十二年(616),慧乘奉诏“于东都图写龟兹国檀像,举高丈六,即是后秦罗什(鸠摩罗什)所负来者,屡感祯瑞,故用传持,今在洛州净土寺”。[15]
隋炀帝奉僧人法济为门师,在皇城右掖门旁临近黄道渠的地方建造龙天道场,“即炀帝门师济阇梨所居”。[16]隋炀帝送给他白马,他经常骑着这匹马出入洛阳皇宫。大业四年(608)法济去世,隋炀帝废朝致哀,百官素服悼念。东都王公大臣至于平民百姓,为法济的丧事制作大幡四十万面,每天斋供百僧,过完“七七”。人们施舍的绢帛,总共有十多万匹之多。
五 隋代洛阳地区的道教
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的半年前,即北周大象二年(580)的六月,他借辅佐朝政之机,以周静帝的名义下了一道诏令:“复行佛、道二教。旧沙门、道士精诚自守者,简令入道。”[17]这是对此前不久周武帝废除佛教的否定,佛教要复兴了,道教也一并恢复。开皇二十年十二月辛巳(二十六日,601年2月4日),隋文帝诏令全国,对于佛教、道教一并保护、扶持。这份诏令说佛法高深精妙,道教冲虚融通,都在播撒大慈大悲,帮助、解救众生,因而众生无不蒙受佛教、道教的保佑、庇护。那么,今后“敢有毁坏偷盗佛及天尊像……者,以不道论。沙门坏佛像,道士坏天尊者,以恶逆论”。[18]洛阳的道教便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恢复起来。
隋炀帝也尊奉道教。他任扬州总管时,在设立两个佛教道场的同时,还设立玉清、金洞两个道教道场。唐末道士杜光庭《历代崇道记》说:“炀帝迁都洛阳,复于城内及畿甸造观二十四所,度道士一千一百人。”[19]隋炀帝在长安、洛阳两都及巡游各地,无不带上佛教的比丘(和尚)、比丘尼(尼姑)和道教的道士、女官(女冠),叫作四道场。他在洛阳,罢朝后常常在西苑游玩,在小树林和亭榭间盛设酒宴,比丘、比丘尼、道士、女官聚为一席,其余隋炀帝的宠姬、皇亲各为一席,杯觥交错,品尝美味。滑州(治今河南滑县)人薛颐,“大业中为道士,解天文律历,尤晓杂占。炀帝引入内道场,亟令章醮(设坛祭神)”。[20]大业年间已迁都洛阳,薛颐所在的内道场是洛阳的内道场。但隋炀帝对道教的崇奉,远不如对佛教那么虔诚,除了他服膺佛教、取得了菩萨戒居士身份的缘故以外,还在于他发现道教徒在合炼丹药以求长生不老方面露出破绽。
洛州嵩山道士潘诞自称已经三百岁,为隋炀帝合炼金丹。隋炀帝让潘诞享受三品高官待遇,为他修葺嵩阳观,建造华丽的堂屋数百间,以童男童女各一百二十人供他使唤。潘诞说合炼金丹,需要石胆、石髓作为原料,于是隋炀帝征发石匠在嵩山开采数十处深数百尺的大石坑,折腾六年,金丹依然炼不出来。隋炀帝问起来,潘诞回答说:“无石胆、石髓,若得童男女胆髓各三斛(一斛为十斗)六斗,可以代之。”隋炀帝看出潘诞是个欺世盗名的大骗子,不禁盛怒不解。大业八年(612),他因指挥收复辽东故土的战争驻跸涿州(治今河北涿州市),将潘诞押来处死。潘诞临刑时,还在玩弄骗局,说:“此乃天子无福,值我兵解时至,我应生梵摩天。”[21]道教把追求羽化登仙比喻成蝉蜕,说修仙者的肉身死亡是“尸解”,像蝉脱壳化出新的身体一样,修仙者由尸体发生解化,从而变成仙人。潘诞把自己被兵器处死解释成是自己的“兵解”,自己即将以仙人身份上生梵摩天(佛教所说的一种天界),然后感叹皇上太没福分,恰恰赶在自己没时间解决皇上长生的问题时来找自己解决问题。
西晋末年,洛阳道士王浮利用前代“老子入夷狄为浮屠(佛陀)”的谎言,编造了一卷《老子化胡经》,经南北朝至唐代增为十卷。敦煌唐代写本说:“[周]桓王之时,岁次甲子(公元前717年),一阴之月,我令尹喜乘彼月精,降中天竺国,入乎白净夫人口中,托荫而生,号为悉达。舍太子位,入山修身,成无上道,号为佛陀。”[22]这是说老子的弟子尹喜,由老子授命,投胎到迦毗罗卫国国王净饭王王后的腹中,出生后为太子乔答摩·悉达多,老子西行进入该国,教化这位太子而成为佛。道教徒常以这部伪经来和佛教争高低。隋朝重臣越国公杨素来嵩阳观,看见老子化胡壁画,冷言冷语讽刺道:“何不化胡成道,而成佛乎!”这个漏洞被揭露,“道士无言”。[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