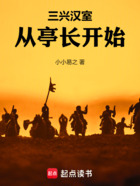
第33章 诈欺
“为何要杀赵谦?”
短短几个字如同一声惊雷,在刘珩脑中骤然炸响。
巨大的惊吓之下,他差点无法维持脸上的正常神色。
然而,就在电光火石之间,刘珩又猛然察觉到不对。
如果刘陶真的确定是自己杀了赵谦,那么今日来到蚩尤里的绝不会只有这么点人,他刘陶更不可能在这里跟自己废话!
他在诈我!
想到这里,刘珩心中瞬间松了口气。
意识重新掌控身体后,才忽然感觉后背发凉。
初春时节,他的后背竟已被冷汗打湿。
好在,从惊恐到怀疑再到镇定,整个过程说起来复杂,却只发生在须臾间,他终究没有露出破绽。
这并不容易。
应该说,能够在极短暂的时间内想通其中关节,难度其实非常高,根本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如果不是穿越时刘珩身上发生异常变化,他绝无可能如此迅速的反应过来。
尽管心中恼怒面前老者不讲武德,但刘珩还是只能装作一脸茫然:
“杀赵谦?谁杀的赵谦?”
说完之后,他好像刚刚反应过来似的,声音突然变大,“冤枉啊刘侍御史,我怎么可能杀害本县县君啊?我跟县君无冤无仇,怎么会杀害他呢?!”
话说的语无伦次,像是蒙受了极大冤屈。
自众人离开塾室后,刘陶就一直盯着刘珩。
见他在自己的诈欺之言下,并没有露出任何异样,刘陶心中不免开始自我怀疑起来。
真的是诈欺之言。
根据目前查到的信息,以及今日所见所闻,刘陶心中隐隐有种直觉——刘珩跟赵谦之死有关联。
但事实上,他手里没有任何一个能够证明赵谦是被刘珩杀害的证据。
刘陶心中不停思量,见刘珩终于安静下来,这才缓缓开口:
“初见你时,老夫就感觉你心神不宁焦躁不安,如果不是你杀了赵谦,那么,你究竟在害怕什么?”
“刘公没感觉错,最近这段时间小子的确心神不宁,时常焦虑躁动,乃至恐惧不安。”
刘珩叹了口气,说话时竟带了几分真情实感,“但小子恐惧的根源,是感觉天下越来越乱,担心贼匪再次袭扰乡里而已,跟县君并无半点关系。”
“你不必如此防备。”刘陶忽然轻笑一声,“既然选择在暗室交谈,老夫就没想把你怎么样。提及此事,对你来说应该是个大好事。”
“好事?”
“正是!你可知如今朝堂之上,宦官跋扈专权?”
我当然知道。
我还知道宦官会继续跋扈下去,直到灵帝早崩呢。
刘珩心里嘀咕,面上却不显,只是茫然地摇了摇头。
以他现在的地位,知晓朝堂之事是不正常的,不知道才正常。现今可没有那么多信息传播渠道,想要了解本县以外的事物,大多只能通过他人转述的方式。
“而今圣天子受奸人蒙蔽,宠信阉宦,以至于其党羽祸乱天下,荼毒生民,那赵谦就是宦官党羽之一!所幸朝中尚有忠义之士,正艰难抗击权宦。二者之间,已经到了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地步。你杀死赵谦,阉宦自然恨你入骨,可对我等士人来说,则是大功一件。如果你愿意,老夫可以将你收入门墙,不但庇佑你不受阉宦迫害,还可以教你经史典籍,助你平步青云!”
刘陶轻抚胡须,满含笑意的看着刘珩。
“刘公所言当真惑人心魄。”刘珩面露异色,“虽然小子很心动,很想成为刘公弟子,甚至都有点想要欺骗刘公了,但......”
他十分遗憾的摇了摇头,“但小子虽然读书不多,却也知晓人生在世诚信为本的道理,没有做过就是没有做过,实在不敢欺瞒刘公啊。”
“你这是看不上老夫?”
刘陶面现不悦,瞪着刘珩说道:“老夫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却也家传《欧阳尚书》、《颜氏春秋》,即便在遍地大儒的洛阳,也能被人称呼一声‘硕儒’!”
“就算你看不上老夫,那也没事。弘农杨氏总该知道吧?四世三公的大族!我和杨赐杨太尉很熟悉,可以引荐你拜入他的门下。到时候,别说郡县里的官职,即使朝堂上的高位,你也未必没有机会啊。”
刘珩愈发遗憾,却依旧摇头。
刘陶终于变了脸色:“你这竖子,不识好人心!错过这次机会,宦官党羽找上门来,你该如何是好?到时候别说你自己性命难保,就是整个蚩尤里刘家,怕是都难逃一劫!”
“小子惭愧,但处世之原则决然不能动摇,否则日后就算窃夺高位,小子也寝食难安。”
刘珩轻轻叹了口气,“何况,宦官虽然势大,却也不能凭空污人清白吧?!”
见刘珩始终不认,而且整体反应、表现,均十分合理,没有任何一点异样,刘陶心中终于彻底动摇起来。
难道赵谦的死,真的跟他没关系?自己的直觉出错了?
至于说,直接把刘珩抓起来严刑拷打一番,刘陶却是从来没想过。
实际上,他根本不在意赵谦的生死,甚至可以说,赵谦这种人死了,他其实很开心。此前关于士人和宦官争斗激烈的话,刘陶没有说谎,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确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
他之所以来到安邑县,之所以出言试探,归根结底只是想要维护朝廷律法的尊严——杀人者死。
没有证据,仅凭猜测就把人抓进牢狱,严刑逼供,这样的做法哪里是维护法律尊严?
刘陶思绪有些飘忽,一时沉默下来。
他不说话,刘珩也没再开口。
两人一时无言。
屋子里竟就此变得沉寂。
良久之后,刘陶方才收回思绪,问道:
“拜过老师么?”
刘珩老老实实摇头:“没有。”
“读过经书么?”
“只读过尚书。”
“《欧阳尚书》?还是《大、小夏侯》?”
“都不是,小子只读过原本《尚书》。”
“读到什么程度了?”
“能背诵全文,但书中真意,都只是自己猜测的,不知是否正确。”
“能背下来,已经很难得了。”刘陶语气平淡,“以你所见,尚书通篇两万五千余字,概括下来主要讲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