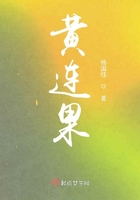
第2章 |竹林出世
自古道兵匪一家,欺压百姓。二十世纪初湖北地方有直系军阀、北洋军阀、皖系军阀等互相混战、争霸;各地土匪猖獗,平时,不是战争就是土匪抢掠,兵连祸结,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不得安宁。人心惶惶,经常跑反、逃难。相隔几天就会出一次妖风:“土匪来了!”,“军阀打仗了!”妖风一起,大村上的人便担惊受怕地都跑到小山沟里躲起来。等到土匪、军阀兵走远了才敢回家。
这些地方的老百姓一提到军阀、土匪,便谈虎色变,闻风丧胆,惶惶不可终日。
1918年深秋,在一个秋风萧瑟,红叶纷飞的日子里,黄家屯人刚刚吃过早餐和往日儿一样三五成群地走向田野,突然有人高喊:“军阀兵来了!打仗了!”
村里人如惊弓之鸟,惊慌失措,奔走相告:“这次真的军阀打仗了,逃命重要,赶紧跑!跑!”
人们扶老携幼,背米袋提包袱,牵牛赶羊,哭着喊着向村后的树林中跑去。如鸟飞兽散,一会儿村上的人都跑光了。家家锁门闭户,十室九空,如一潭死水。
唯独黄建财夫妻俩还没有逃走,因为黄建财妻子有孕临盆,只能居家不出。他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家团团转。若真的打起仗来,包括未出世的孩子,一家三口准遭殃!左思右想,觉得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还是离家出走。他们慌忙找来些换洗衣服,带些零钱,锁好门窗,丈夫搀扶着妻子慢慢地离开了家,向村后的树林深处走去。
在曲折蜿蜒的山谷中走着,前进缓慢。大约走了三四里路,他妻子再也走不动了。于是只得在树林深处的一撮竹窝里,选择空地坐下歇息。忽然间他妻子说:“我肚子痛了。”
“这怎么办呢?肯定是要分娩了。”黄建财慌了手脚,无计可施。
一会儿他妻子的下身流出了一阵血,一直淌到鞋袜上。建财眼睁睁地看着,束手无策,这里无人,也没有接生婆,更没有热水。一个大男人怎么会做接生这种事儿呢?
叫天天不灵,叫地地无声。在这十万火急之中,他抱来一些干茅草铺在地上叫妻子躺在上面。妻子一阵阵剧烈疼痛。由于在跑反途中,又不敢大声呻吟,只能咬紧牙关忍着痛。唯见她哭丧着脸,周身大汗淋淋,头发如洗,处在生死关头。在这万分焦急之中,一刹那只听到“哇!”的一声,妻子生下一个女婴,掉在裤裆儿。丈夫忙帮妻子脱下裤子,小东西精光的身体呱呱坠地,滚在茅草上。血淋淋的沾了一身竹叶、草末、泥巴。两小脚乱蹬,张着小嘴不住地哇哇啼哭。
“唉哟喂!你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来到世界上?该你受苦了!”黄建财双眉紧锁,唉声叹气,没有主张。没有盆,没有水,没有剪子,没有衣服。在这万般无奈之下,做母亲的只能用自己的牙齿给婴儿咬断了脐带。
秋风飕飕,小东西冻得发抖。也没有洗,抓一把乱茅草给她擦了擦,沾满的草末、泥巴也来不及清理。母亲脱下一件外衣血淋淋的将婴儿包裹着,用茅草绳子五花大绑捆扎了起来。
这时树林外面又传来喊声:“军阀兵来了!打仗了!”炮声轰,枪声紧、喊杀声渐渐逼近。黄建财只得再次搀扶起妻子艰难地向前走。在深深的草丛中走了好一阵子才找到一条羊肠小道,他们沿着这小道向一个叫北山沟的小村走过去。
妻子在山路上留下一个个血脚印,路上女婴不断地啼哭。远处的战斗号角声、枪炮声越来越近,喊杀声十分惊人。在这万分危急之时,黄建财害怕婴儿的哭声被当兵的听到了,会引来杀身之祸。无奈之下果断地说:“快把小孩扔池塘里吧!扔池塘里吧!大人逃命要紧!”
做母亲的哪里舍得?这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而且是头胎,怎么忍心造这个孽?她哭诉着,骂道:“你缺德!不是你生的是吧?哪有这样做父亲的呀?有道是虎毒不食子,你不通人性!”
可怜这做母亲的把婴儿紧紧地抱在怀里,用衣服捂着她那小脸,不让她哭出声来。拖着沉重的脚步向前挪动,一步一个血印,好容易又走了三里多路。这对于一个三寸金莲又刚生孩子的妇女来说,是何等的艰难啊!
他们来到北山沟这个小村庄才歇脚。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野外渐渐地灰暗,风更紧,天更冷。他们在一户人家门前停下,慌忙打开衣包看婴儿,坏了,婴儿闷得小脸蛋像熟葡萄一样的乌紫,不哭也不动了。黄建财慌忙用手指试一下婴儿的鼻孔,叹道:“哎呀,没有气了!”摇了摇头说:“没有用了,没有用了,扔掉吧,扔掉吧!”
他妻子“哇”的一声哭了,说:“哎呀!怎么搞的?刚才还在动弹么?这一会儿怎么是这样啥?”母亲边哭边抱着婴儿不断的摇晃,摇晃,再也舍不得扔掉。
过了一会儿小嘴巴终于微微动了两下,犹如小猫叫一样“哇-”的一声哭了,苏醒了,醒了,好危险呀!命不该绝。
黄建财惊喜地道:“哎!好了,好了,死不了,受苦人命大!”
夫妻俩破涕为笑,这才松了口气。
血盆一样的太阳慢慢地沉入西天,风飕飕,灰沉沉,夜幕渐渐来临。王建财向前敲敲这户人家的院门,问道:“屋里有人吗?”
喊了两声院内出来一位老者,建财两手抱拳一拱行了个礼,说:“老人家,我们是跑反逃难出来的,天色已晚,想在贵处借个宿,行吗?”
那老头摇摇头,好像没有听懂建财的话,只发出:“哑,哑,哑......”的声音。大概是个哑巴?建财不方便进去,只得再次叫一声:“屋里有人吗?”
“谁呀?”
谢天谢地,里屋有人答腔了。
建财忙应答:“老乡,是我们呀。”
屋内出来一位中年妇女,穿一件蓝底小素花上衣,一条印花蓝布裤子,头发向后卷成一个皱巴巴(发鬈)。她一脸笑容,看起来很热情、善良。见门外两个陌生人,便和颜悦色地问:“你们是?”
“嫂子,我们那边打仗了,被迫跑反出来。天色已晚,想在你家借个宿,行吗?”
“行行行,哪个不出门呢?何妨这兵荒马乱的逃难。”
说话间女婴“哇,哇”的哭了,那女人惊喜地说:“哟!还有个奶毛?好玩吧。”
这么一问,黄建财只得实事求是地说了:“不瞒你说,这女婴是刚才在竹林里生的。实在没有办法才来投靠你们,请行个方便吧?”
那女的很善良,一边看婴儿一边说:“行,行。可怜呀,这个小宝贝在野外所生,天当被,地当床,将来必定是个有天寿、地福的福姑娘。真有意思,难得,难得!进来,进来,宿我家吧......这?这兵荒马乱的......到?到哪里去,去呀?但是......”
说到这里她却吞吞吐吐的停了下来,显示出很为难的样子。下面的话不言而喻,建财领悟了她的意思:在农村里有迷信思想,认为刚生孩子的妇女未满月不能进别人家的门,会给人家带来晦气。
建财忙说:“哦,哦,我知道了。哪么你家有没有闲置的小屋、偏房吗?给我们暂住下就行。”
“有,有,你来看看,行不行?”
黄建财夫妇随着进了院子。院子西边有间小屋是牛棚,还放了些杂物。因为长时间不住人,自然有股霉气和牛粪味,屋内布满了蜘蛛网。
那妇女说:“只要把这些杂物搬出来再打扫一下,就可以开铺了,委屈你们,将就将就吧?”
王建财说:“行行行,出外由外,有个落脚地就行了,还讲究什么条件?”
那妇女、老头和建财三人把那些杂物全部搬了出来,清理打扫了一下。抱来干稻草铺了张地铺,主人拿来被单,棉絮往上面一铺;老头拿来煤油灯、便桶、水瓶、洗面盆等。
“你们看,行不行?”
“可以,可以,多谢大嫂费心了。”
“不用谢,条件不好,请将就着吧。这里就当作是你们的家,吃喝我送来。苦一点不要怪,打完仗,当兵的走了,平静了再回去。”
“谢谢!谢谢!”
黄建财夫妻俩不住地道谢,为难之时能遇上这样的好人也真算是走运了。便乐意与牛同舍住了下来。
那女的转身去了。她手脚十分麻利、快捷,一会儿端来饭菜,说:“请两位先充充饥吧,没有好招待,出门不能饿着肚皮呀?”
“谢谢,谢谢,给你添麻烦了。”谢过主人,夫妻俩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确实饿了,简单的饭菜吃得特别香。
过了一会儿女主人找来些她小孩的衣服,给女婴洗过澡,穿了衣裳。又端来黄连水和红糖汤,笑嘻嘻地说:“小女孩初食人间烟火,先给她吃一口黄连水,愿小女儿先苦后甜,一生平安。”
“谢谢,谢谢”,黄建财夫妻俩不住地道谢。
女婴尝到黄连水,苦,张着小嘴巴便哭,惹得大家嘻嘻地笑。她又喂红糖水,嘴里念念有词:“第一口糖水喝了,愿女孩一生平平安安,茁壮成长;第二口喝了,愿她一辈子甜甜蜜蜜,永远幸福;第三口喝了,愿她长大成人后嫁个如意郎君,白头偕老。”接连许了三个愿,诚心一片。
“哎哟,托福,托福。谢谢大嫂的好意,谢谢。”听了一阵祝福词,黄建财夫妻俩非常高兴、感激,喜笑颜开。
打那时起,一日三餐天天都由女主人送过来,不厌其烦,细心照顾,嘘寒问暖,无微不至。
主人虽好,但牛棚毕竟是牛棚,虽已深秋,天气转凉了,可是晚上蚊子依然嗡嗡叫着,一把掠过去能抓住好几只。稻花蚊子铁钢嘴,咬人厉害,三人的身上尽是蚊虫块。特别婴儿,全身布满了红点点,小脸蛋红肿得像红萝卜;因为地铺,又潮湿,身上长满了虱子,被絮上、棉袄上许多虱子,吃得胖胖的一饱血;住在牛舍,身上一股牛粪味,直充鼻孔。
欢乐的时光一向是过得特别快,而痛苦的日子是难熬的。做母亲的夜里给孩子喂奶把尿,加上蚊虫叮、虱子又咬,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在那牛棚里度日如年,整整挨了半个月。待到打仗结束,风平浪静才回家。
临走时,建财过意不去要付些饭菜钱,主人执意不收,她说:“什么饭菜钱,这里又不是住饭店,要你买单。我没有好招待,提起来真羞人。如果不嫌弃,我们结为亲戚走走倒是桩好事。”
黄建财见她善良、厚道,觉得此人交得。便满口答应:“好好好,结门亲戚,结门亲戚。”
还是他妻子反应快,忙说:“哪么,就让小丫头拜你为干妈吧?”
女主人高兴地说:“太好了,我就是缺少个女儿,有个干女儿走走再好不过了。”说罢她转身回屋去了,片刻拿来两块大洋,顺手在门对联上撕下一片红纸儿包着塞进婴儿身上,说:“我给小宝贝一点贺礼,祝她长命百岁!”
“不能收,不能收,在这里吃住多日,你们分文不取,怎么能又吃又带呢?”建财推辞不收。
“那是另外一回事,这个是我给小女孩的一点儿心意。收下吧,别把我这个干妈当铁公鸡,一毛不拔。”
女主人执意要给,黄建财推辞不了,便说:“谢谢孩子的干妈。孩子长大了一定来感谢你这个好心的干妈。”
“好,好,我们期盼那一天的来到。”
双方情义深笃,在依依不舍中道别。
温润的清晨,曙光初照,朝霞把每一座山头、每一片地面都抹上一层粉红的薄纱,温柔、瑰丽得令人瞠目。在此美好的时光,黄建财夫妇把这个宝贝女儿带回了朝思暮想的家。
回家后全村人都来看热闹,大家都称赞野外生子是个奇迹。
黄建财给女儿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黄蕾”,即将绽放的花蕾,多美丽呀!而他妻子却执意不从,说:“不好!不好!什么‘黄蕾,黄连’的?‘黄连’多苦吗?一辈子吃不完的苦!我叫他‘竹林’,竹林是她的出生地,值得纪念。梅兰菊竹四君子之一,叫起来既好听又有意义。”
黄建财没有听妻子的话,去祠堂里报户口还是给女儿取名为黄蕾。而他妻子却一直唤他黄竹林。有时也调皮地叫她“咬脐丫”、“牛棚蚊子”、“稻草虱子”等等,这些都是她难忘而痛苦记忆,一直把这个苦月子深深地记在心坎里。
后来“黄蕾”,“黄竹林”很少有人叫,而“咬脐丫”这个奶名很快在村上传开了。到了十六七岁成了亭亭玉立的美女,人们仍然喊她“咬脐丫”。她出生时的传奇故事也广为流传,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柄罕闻。
咬脐妈妈含辛茹苦地抚养着咬脐,咬脐也天性健康,茁壮成长。十多岁便是一位亭亭玉立的姑娘,白里透红的皮肤显得很有光彩;一头乌黑而自然的美发闪闪发亮;高高的鼻梁上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和黑葡萄样的眼珠,十分有神;红红的嘴唇能说会道;笑起来两只酒涡,惹人喜欢;身材高挑,曲线柔美;热情爽朗,天真无邪,玲珑剔透。人称小精灵,十分可爱。
咬脐的爸爸一直在外面做小生意,经常不在家,小咬脐陪伴着妈妈,母女俩相依为命。
她聪明伶俐,小嘴巴能说会道,五岁就能和大人对答如流。她勤奋好学,遇事总要问个为什么?因此她很懂事。从小欢喜画画,母亲买支铅笔给她学画,只几天功夫,她画的花、草、狗、猫等就有好点儿像。母亲非常喜欢这个闺女,又疼又爱,视她为掌上明珠。八岁那年,咬脐妈对她爸说:“竹林聪明,你把她送进学校读书吧?”
她爸瞪着眼睛骂道:“不读!女子无才便是德,读书反而害了她。这兵荒马乱的年代,又是乡村女孩子,读什么书呀?不读!”
“重男轻女!封建伦理!”咬脐妈妈想女儿出人头地,不读书有何出息?从心底里恨透了她爸。
这也难怪,当时社会男尊女卑,山旮旯儿很少有女孩读书。用农民旧思想的话说:“女生外向,总是要嫁人的。读书也是给别人家读的,花钱也枉然。”为了咬脐丫读书的事,夫妻俩曾狠狠地吵过一架。因经济大权在男方手里,女的败北。因此咬脐没有进过学堂门,斗大的字不识一个。
咬脐心灵手巧,十岁那年冬天,她妈妈在做鞋,她一旁看着学做针线,很快,什么纳针、缭缝针、锁边针等都学会了。接着又学会了纳鞋底、做鞋帮、上鞋底等,因此她十多岁就会做鞋了。后来慢慢地做得更漂亮,更结实,更合脚了。
后来在妈妈的指导下又学会了绣花,什么鞋头花、枕头花、窗帘子花等等,越绣越好。构图新颖,色彩鲜艳,很有神韵。超过了她妈妈,真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一天母亲问女儿:“竹林,你做的花色彩搭配得这么好,是跟谁学来的呀?”
咬脐笑着说:“我看院子里鲜花配的色。”
“哪你图案怎么学会的呢?”
“我觉得做多了太繁琐,密密麻麻的不好看。能简则简,留点儿空间,只须做几朵花配几片叶反而好看些。”
看来绣花和画花一样,也注重写生、配色,讲究构图。咬脐聪明伶俐,自学成才。她妈妈心里乐滋滋的佩服女儿,为有这样的女儿而高兴和骄傲。
很快咬脐的做鞋、绣花在村上颇有名气,很多姑娘都乐意和她交朋友,跟她学做鞋、绣花,组成了一个针线小组。
咬脐的父亲黄建财也聪明、能干,心眼儿活泛。年轻时一直在外行商,做点儿鞋帽生意养家糊口,日子过得平平。自从八国联军侵华后,各国的商界把中国看作肥羊肉,大市场,千方百计到中国来推销他们的商品。国人把这些外国商品叫“洋货”,什么洋布、洋伞、洋肥皂、洋火、洋油、洋蜡烛等等,几乎日用品都姓“洋”了。
中国人民抵抗外国侵略者,也抵制“洋货”。但在当时的社会状态下越是抵制越是销得快,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是社会发展规律,先进的总是要代替落后的。比如火柴:几千年来,中国农村老百姓家里传统的取火方法是用火刀打火。用一块铁片叫“火刀”,一块黑色的石块叫“火石”,用表芯纸卷成的纸条叫“媒纸”。打火时把“火石”与“媒纸”紧紧掐在左手虎口里,右手握着“火刀”去打“火石”。打几下,甚至十几下,打出来的火星溅到“媒纸”上,“媒纸”传上火星,再趁机吹几口气,便引来了火。若遇上阴雨天就打不来了,很不方便,吸烟人往往因此而唉声叹气。
有了火柴,情况大不一样。取一根火柴棒一擦,火便来了,方便而快捷,何乐而不为呢?
又如肥皂:当时落后的农村妇女们洗衣服是用热水去过滤新鲜的稻草灰,用过滤出来的水去洗衣服。大概稻草灰中含碱,滤出含碱的水能除去衣服上的油脂的道理。但用这方法洗的衣服呈灰色的,混浊不清,洗衣也很麻烦。有了肥皂情况就不同了,只须在衣服脏处抹些肥皂搓一搓就干净了。
尤其那外国的花洋布,质地薄而细腻,花色多,不退色。穿着透气、轻柔、凉爽而漂亮;当时农村的家织土布粗糙、厚硬,而且不牢;花色也只有条子、格子或单色印花,叫印花布;水洗时会掉色,穿着不舒服,远远比不上花洋布。因此花洋布的出现,妇女们争先恐后去抢购,十分热销。
多种原因当时的“洋货”受人青睐,成了时尚、热销商品,悄悄地在我国城市、农村流行起来。这自然给那些不法商带来赚钱的好机会。
黄建财抓住了这个有利商机,偷偷地做起了“洋货”生意。他从芜湖、无锡、南京等地进那些日用品“洋货”,到湖北农村偷偷推销,生意好极了,赚钱厉害。只几年功夫就发了点小“洋财”,买了田,雇了长工;做了一颗印的大住宅,并修建了漂亮的后花园。园内修了小桥、水池、假山、石道等;栽有月季花、鸡冠花、牡丹和芭蕉等各种花。一个小小暴发户的庭院并不亚于大员外家的庭院。
小咬脐非常喜欢她家的家业和庭院,整天洋洋得意地在院子里玩耍。她对这里的花草极端迷恋,成了一个爱花如命的小园丁。很快学会了栽花、嫁接和施肥、浇水等技能。她栽的美人蕉、紫罗兰、凤仙花、月季等都长的都很好。每到夏天她用凤仙花染指甲,也帮母亲、妹妹染,她的心思优雅细致。
而她母亲却惶惶不可终日,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因为她经常听到外面人风言风语说:“黄建财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里搞‘洋货’生意,国难当头时他竟然吃里爬外,为富不仁,违背良心去发国难之财,总有一天要倒霉的!”
黄建财妻子担惊受怕,劝丈夫不要做这种生意,他当耳边风,继续去做,并越做越红火。
请来的长工孙师傅是本村人,为人本分,做事踏实。几十亩田地由老孙打理得有条有理,唯一能帮忙的也只有小咬脐了。农忙时送饭、送茶,下蚕豆、碗豆、麦子等种子,都是咬脐的事。到后来车水、栽秧咬脐都学会了,做农活她不亚于男儿;家里挑水、推磨、砍柴、浇园都是咬脐做。她里里外外一把手。虽说是暴发户的大家闺秀,并没有员外家千斤小姐那般娇生惯养,而是田地里,磨坊里忙个不停的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女儿。
母亲见她能干,既高兴又心疼。
孙师傅觉得田多了人手不够,如果再雇长工划不来,想来想去,如果是有头牛比较好,有牛耕田人轻松多了。一天他对老板说:“老板,田多了一个人种不下来,买头牛吧?有牛既节省劳力又能积些肥料,一举两得。”
黄建财觉得老孙言之成理,便答应说:“老孙,你说得对,和我想到一处去了,我也想买头牛。请大伙给打听打听哪里有牛买?”
几天后黄建财真的牵回来一头牛。他将牛拴在门前的大榆树下,一会儿来了很多人看热闹。大家围着牛,七嘴八舌,对牛品头论足。那是一头四颗牙的公牛,全身黑油油的毛,骨粗、膘肥、肩厚、四肢发达,身强力壮。
二叔说:“这牛调养得好,年轻,才四颗牙,肯定有劲。只是还没有学会耕田,你看它肩上毛发无损,没有上过犁绳似的。”
黄建财说:“听卖主说它已学会了耕田,而且步子走得很稳当。”
孙师傅品议着说:“这牛已耕过田了,看它的肩膀肌肉发达,是用过力的肩。可能不那么乖巧,有脾气,它的眼珠是突出的,常沉着头偷眼看人,一付凶相。”
“对对,卖主说它爱唬人,要防着点。”
二叔说:“哎呀,这牛唬人,胆小的人不敢靠近它。建财呀,你必须请一个能干的放牛郎哟?”
“我想暂时叫小丫头咬脐放着,待到农忙需要割草喂牛,再请放牛郎。”
二叔说:“你拉倒吧!11岁的小丫头能放鹅,放鸭,最多也只能放羊。这样的烈性牛,她敢放?”
老孙说“老板怕花钱请放牛郎,就叫咬脐来试试。”
黄建财点点头,便朝屋里喊:“丫头,来,我给你买来一个好玩的东西,你来看看。”
咬脐和妈妈一同在屋里忙做针线活,听爸爸一喊便很快往外跑。她妈也好奇地跟女儿后面来了。
小姑娘高兴得一蹦三跳地跑了出来。见门外这么多人不知何事,她把舌头一伸,耸耸肩,想退回屋去。刚好与她妈相撞,便挽着妈妈的手臂一道出了门。
黄建财说:“丫头,我给你买来一头好玩的牛,你高兴吗?”
初生的牛犊不怕虎,咬脐认为牛和小兔、小羊一样温顺、好玩,她哪里知道牛这么凶狠!好奇地去抓牛绳,牛头一沉,瞪着双眼,向她唬来。咬脐吓得哇的一声尖叫,回头就跑,她妈慌忙搂住丫头,骂道:
“没事找事!为什么买头牛来吓丫头?吓病了再找你算账!”
这一幕惹得大家哈哈大笑。咬脐从妈的腋下露出半张脸,不住地摇手,再也不敢靠近牛了。二叔笑着说:“我说嘛,丫头毕竟是丫头,个个都胆小,怎么敢放这烈性牛呢?你必须找个能干的放牛郎。”
黄建财说:“是是,看来不请放牛郎是不行的了。”
孙师傅却丧气地说:“哎哟,老板呀,本想给你省一点,谁知反给你找来麻烦了。”
“没事,没事,迟早要请人。请大家帮忙打听打听,请个放牛郎回来吧。”
大伙点点头,慢慢地散去了。
时年11岁的小咬脐--黄竹林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听爸爸说要请个放牛郎回家,这倒是件新鲜事儿,家里将要添个人口,真有意思!她高兴极了。
咬脐五岁那年她妈生了个二胎,原本想给咬脐添个弟弟,结果违拗心愿,还是生了个丫头。今年七岁了,取名梅林。平日里爸爸不在家,妈妈带两个小丫头在家,这么大的宅子确实笼罩着寂寞空虚,实在冷清。
这天晚上咬脐靠紧在妈妈身边,好奇地问妈妈说:“妈妈,听爸说我们家将要请个放牛郎回来,放牛郎是什么样的人?是男的还是女的?请来了做些什事呀?”
“放牛郎一般是男孩子,除掉放牛、割草、做农活外,家里事还要扫地、挑水、推磨、浇园、带小孩等家务。”
咬脐把肩一耸,伸伸舌头,惊奇地说:“一个小孩能做这么多事,我才不信呢?”
“那当然嘞,什么叫‘帮工’?帮工就是受苦辛,端人家的碗受人家管呗,什么事都叫他做。这个世道,家里穷了就倒霉!”
小咬脐听了这番话觉得老天爷不公,有钱孩子读书,无钱孩子帮工;富人享乐,穷人受苦。她双手牵着妈妈的手摇晃着,说:“妈妈,放牛的来了你可不能那样狠心待人,要当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好不好呀?”
妈妈用手指在咬脐额上点了一下,说:“你放心,妈妈不是恶人,会善待人的。”她感到女儿从小就有一颗善良的心,甚是高兴。
咬脐又问妈妈说:“妈,放牛郎识字吗?”
“傻丫头,没有请回来哪里知道?一般帮工的孩子都是穷人家的,不读书,认字的少。”
咬脐的嘴巴一翘多高,十分沮丧地说:“哎呀,要请来的放牛郎认得字就好了,可以教我认字呀。”
女儿的心事当娘的自然知道:她渴望读书识字。当年没能上学读书,成了她终生的遗憾。女儿沮丧的神态勾起了娘的心疼。
对待这未来的放牛郎各有各的要求。
孙师傅想要一个年龄大的,劳力强的,除了放牛以外,田地里能帮他做农活。快手不敌帮手,说起来一个长工种这么多田,名声好听呗。
黄建财想找一个能制服烈性牛的孩子,天天把牛喂得饱饱的,膘情不减就行了。
咬脐的妈妈想法又是一样。因为丈夫经常不在家,只有自己带两个小女孩在家里,既冷清又害怕。家里发了点“小洋财”,惹人眼红,若小偷进门偷盗,那就纰漏了。她希望放牛郎有点儿手脚功夫,既能放牛做家务,还是一个看家护院的保镖--“牛郎保镖”,多好呀?
而咬脐丫,黄竹林却日夜向往来一个识字人,最好琴、棋、书、画样样会,既是一位放牛郎,又是一位家教先生。跟他学习文化,提高自己的能力,有多好呀?她想入非非,沉醉在美梦之中。
到底请来一个什么样的放牛郎?能满足谁的要求?大家都在期盼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