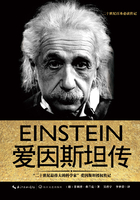
十九世纪末的科学观念
在机械物理的黄金时代,人们普遍认为机械论适用范围之外的领域是未知且不可知的,因为“理解”意味着“能用某一机制来说明”。1872年,德国生理学家、实验电生理学之父杜波依斯—雷蒙德(1818—1896)在他的著名演讲《我们对自然认识的界限》[6]中提出,如果“理解”意味着能够回溯到“牛顿力学定律”,那么至少就存在两个科学上的关键问题明显无法用牛顿定律解释。其中之一是,当力发挥作用时,空间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另一个问题则是,人们在思考时,大脑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过程。通过这两个例子,杜波依斯—雷蒙德承认确实存在人类知识范围内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ignorabimus),而不是“我们现在不能回答”(ignoramus)。因此,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成为科学失败主义者的标签,鼓舞了反科学的趋势。在十九世纪末,生物学和物理学实验中发现了更多无法用牛顿定律解释的事实,“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很快升级为一条更有煽动性的标语:“科学的破产”(“The bankruptcy of science”)。
这种对理性科学思想的挫败感在各种社会事件中被放大发酵。十八、十九世纪时,科学——即牛顿的机械物理——使人们相信社会的发展是不断向前进步的。只要人类用科学的武器武装自己,抛弃迷信观念,就可以满足各种需求。这一思想在政治上体现为自由主义。然而在十九世纪末,基于科学的尝试和对进步的信仰却不能将人们从人口大增长带来的经济衰退中解救出来,也不能宽慰人类个体心灵的痛苦,一种绝望的情绪和对科学理论实践的失望蔓延开来。除自由主义之外,新的政治潮流孕育了有别于机械论的科学观。其中一种趋势是退回到中世纪的有机科学观,这孕育了独裁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另一种思潮的代表人物为卡尔·马克思(1818—1883)他将机械观的唯物主义转化为辩证唯物主义,其逐渐发展为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
当然,人们仍然不可能否认科学是科技进步的基础,但是科学却遭到贬低和诋毁,就像教皇对哥白尼世界观体系的贬损:机械观的自然科学只为人类的行为提供了有用的指导,而不是自然的本质。1900年左右,法国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阿贝尔·雷伊(1873—1940)对这种绝望情绪笼罩下文明社会所面临的危机做出了准确而尖刻的描述:“如果这些曾经解放人类思想的科学在危机中沦为技术的小把戏,而不是自然灵感的迸发,这将掀起一场彻底的革命。我们原本认为物理学带来了思想的解放,而这将是最致命的巨大错误,应当是一些主观的直觉和神秘的存在带来了思想的解放。”
在机械观科学体系的崩塌中,有两种拯救科学于危机的方法。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利马(Antonio Aliotta 1881—1964)在他的《对科学的唯心主义反应》(The Idealistic Reaction against Science)中描述了这一处境,提出要么和叛逆者尼采一样,诉诸思想的非理性,回归道德主义或浪漫主义,让意志成为思想的源泉,凌驾于理智之上;要么承认科学体系的不足,寻找并尝试新的科学理论。而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拥护者选择了第二种方法,他们认为机械观科学解决问题的方式必将导致其自身进入死胡同,因为它没有正确定义科学的目标。那些不能解决的“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的问题如同幽灵和幻影一般,与科学本身并无关系。欧洲的马赫和庞加莱、美国的皮尔斯和杜威等人,早已证明能否把自然现象归纳到一个特定的科学框架下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科学的内容是否有用,而不是科学用了什么样的语言或什么具体的方程。因此,在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定义里,很显然,十九世纪末的危机不是真正的危机,而是科学在向它的最终目标——创造一种能预测和控制自然现象的工具——接近时的一个阶段。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实证主义—实用主义运动属于反夸大知识作用的一系列思想运动的一部分。这种新的运动,无论是被称作实用主义、实证主义还是工具主义,都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反智运动,因为它们并没有提出无意义的问题。尽管现在还未能发现并建立大统一理论的蓝图,但是“工具”的创造——现代对科学的定义——只有通过知识和智慧才能达成。能量定律、惯性定律等物理定律或许就像交响曲的谱写一样,只能被某个天才发现。但是当一个一般性定律发展成熟后,是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将其发扬推广。只有知识群体能够检验并证明这些原则的正确性,决定其是否在实现科学目标的过程中发挥价值。
十九世纪便在这些思潮中落下帷幕。科学的目标是揭示真理这一信念被动摇,但是取代它的是实证论的清醒认识。科学变得更加灵活,并随时准备好迎接最大胆的假设和挑战。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科学的功能而非科学的哲学意义得到了重视。在熹微晨光的照耀下,希望就像地平线上的银线一般缓缓升起,更精确、逻辑性更强的新科学体系在可操作性基础之上逐渐建立。在这黎明中,二十世纪降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