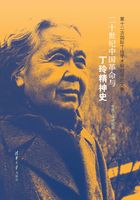
三、追寻女性自我生命价值的实现——丁玲作品中的情爱与革命
在思考女性生命困境、寻找女性生命出路的立场方面,丁玲和她的湖南姊妹白薇是完全一致的。丁玲在1928年出版第一部小说《在黑暗中》,从题目便呼应白薇曾走过的人生道路及生命感受。
《在黑暗中》包含《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和《阿毛姑娘》四篇小说,这四篇作品从不同角度呈现女性所面对的生命与社会困境。丁玲在处女作《梦珂》中即展现高度的才华和敏锐的社会感受,小说透过女主人公梦珂的生命经历,开展出“学校”“姑母家”和“圆月剧社”三个场景,而这三个场景分别代表新女性必定要面临的几个人生问题,包括受教育、爱情与婚姻、职业等。小说将背景设计在上海这个最现代化的大城市中,封建思想与资本主义文化在这里有最激烈的冲突和最高度的结合。整部小说围绕着社会对女性的观看方式和物化问题,学校美术绘画课中代表西方前卫艺术的“人体模特儿”,到了中国被翻转成男性对女体的观看和骚扰,在姑母家,梦珂承受表哥晓淞和澹明对她身体的凝视和欲望,在圆月剧社,梦珂更直接地感受到自己如同商品般被品头论足,像妓女一样被毫不尊重的眼光所观览。梦珂的生命经验,呼应了白薇《炸弹与征鸟》中余彬与余玥的社会体验,也非常精准地掌握新女性进入社会之后所面对最严重的问题。
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丁玲细腻地描写莎菲面对爱情时复杂的心情。丁玲没有白薇那种“五四”式的对于爱情浪漫美好的歌咏,而相较于白薇描写男性与女性面对爱情时态度上的差异、男性对女性身心严重的伤害,丁玲所思考的是更为女性自我内在的问题。她透过莎菲对于苇弟和凌吉士两人反复无常、举棋不定的心情,直视女性面对爱情时精神与肉体、理智与情感的冲突与拉扯,勇敢地说出自我的欲望,也认真地反省自我的软弱与虚荣。同时,她更以“爱情”为出发点,延伸到对于女性自我定位与人生问题的思考,莎菲自省“我,我能说得出我真实的需要是些甚么呢?” 无疑指出了莎菲生命的真正病根。可以和《莎菲女士的日记》合观的是《暑假中》,《暑假中》透过志清、德珍、嘉瑛、承淑几位自立女校的女老师在暑假中对于未来的思考,表现新女性不同的生命出路和精神表征,她们有的期待幸福的婚姻,有的向往热烈的爱情,有的对未来感到消沉无望,有的怀抱着突破现状的热情和梦想。小说末尾,由于校长交付了学校招生的任务,这些女孩便各自忙着要讲授的功课,相较于莎菲生活的无聊空虚和无所事事,相较于这些女孩在暑假中的牢骚情绪,忙碌中的她们最是神采奕奕。这样的结尾意味着女性在工作中所获得的成就感和充实感,相对于爱情、婚姻和家庭,女性也许只有找到自己的人生事业,才能找到安身立命之所,丁玲在此具体地指出女性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工作的必要性,从这个角度来看,丁玲往后的人生会将自我发展与社会革命结合在一起,并不是让人意外的事。
无疑指出了莎菲生命的真正病根。可以和《莎菲女士的日记》合观的是《暑假中》,《暑假中》透过志清、德珍、嘉瑛、承淑几位自立女校的女老师在暑假中对于未来的思考,表现新女性不同的生命出路和精神表征,她们有的期待幸福的婚姻,有的向往热烈的爱情,有的对未来感到消沉无望,有的怀抱着突破现状的热情和梦想。小说末尾,由于校长交付了学校招生的任务,这些女孩便各自忙着要讲授的功课,相较于莎菲生活的无聊空虚和无所事事,相较于这些女孩在暑假中的牢骚情绪,忙碌中的她们最是神采奕奕。这样的结尾意味着女性在工作中所获得的成就感和充实感,相对于爱情、婚姻和家庭,女性也许只有找到自己的人生事业,才能找到安身立命之所,丁玲在此具体地指出女性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工作的必要性,从这个角度来看,丁玲往后的人生会将自我发展与社会革命结合在一起,并不是让人意外的事。
而《阿毛姑娘》则是可以与《梦珂》合观的作品,它同样围绕在女性处境与社会现代化、资本主义商业化之间的问题,但它更具体地写出现代城市的物质生活对女性的诱惑。阿毛姑娘的城市冒险之旅让她无法再满足于现有的农村生活,而城市生活幸福的虚假性却导致她精神上的抑郁和苦闷,最终走上自杀一途。阿毛是来自乡镇的农村姑娘,正与梦珂作为新女性的身份相互对照,但无论梦珂或阿毛,都不能摆脱现代城市生活对女性的诱惑和宰制。从丁玲对《阿毛姑娘》的书写,也能看到丁玲宽阔的社会视野,她在思考新女性的生命出路时,也同时关注不同阶级的女性命运。
从《在黑暗中》的四篇小说可以发现,丁玲最早的创作立基在思考及寻找女性生命价值的实现,这是青春时代的丁玲最重要的生命课题,因此尽管她写爱情,她的爱情却是与自我认识、自我实现等的人生问题结合在一起。同时,她警醒地察觉到女性与现代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因此从个人经验中抽离,去观察和描写不同阶级的女性与社会的互动,从而更清楚地认识社会和女性生命的困境。她在最早的四篇小说中,便同时向内省视女性个体,也向外观察社会,因此当她与胡也频在1928年来到上海,“革命文学”与共产党革命的概念进入她的社会视野之后,她便将女性生命实践与中国社会革命的问题结合在一起。
但这转变是渐进式的,充满辩证性的思考,思考的痕迹留在一向被称为“革命+恋爱”小说的《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之二)》中。从思考女性生命出路和自我实现的角度出发,《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中的若泉和子彬代表两种不同的生命取向和选择,而小说的主线可以说是美琳思考和选择的过程。若泉所宣扬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普罗文学代表20年代末期风起云涌的革命思潮,而子彬拥有“文学”与“爱情”的双重成就则是男性知识分子在五四文学运动与个性解放之后获得的最大幸福。这两种思潮之间具有某种冲突和矛盾,若泉以为像子彬那样的作品是“一些感伤主义,个人主义,没有出路的牢骚和悲哀!……他们的出路在那里,只能一天一天更深地掉在自己的愤懑里,认不清社会与各种痛苦的关系” ,他企图让文学更有益于社会和历史。而子彬一方面认为追赶时髦的革命文学是肤浅的行为,一方面又为自己逐渐被文坛忽视而焦虑万分,革命文学的风潮扰乱了他的心神。在对两人的描写中,未必没有丁玲自我的反省,敏锐而富有热情的她一定在上海革命风潮的鼓动下,在胡也频积极投入的左翼运动中,感到了时代的变局所产生的激动人心之处,可能也因此反省自己早期的作品正流露着“没有出路的牢骚和悲哀”,而正因为这“没有出路”的景况是真实的,所以她必须寻求突围,她以美琳的选择来说明自己的思考:美琳原本的理想是拥有幸福的爱情,但在若泉和子彬的论辩中,她发现自己除了爱情之外一无所有,若泉在十字街头的忙碌和活跃与子彬在亭子间的骚乱和苦恼形成鲜明的对比,她无法再安于“五四”之后所拥有的幸福的家庭生活,而产生了参与社会同时也实现自我的美好愿望。在小说的结尾,一向被子彬认为是温柔娇美的美琳也走向了街头和群众。
,他企图让文学更有益于社会和历史。而子彬一方面认为追赶时髦的革命文学是肤浅的行为,一方面又为自己逐渐被文坛忽视而焦虑万分,革命文学的风潮扰乱了他的心神。在对两人的描写中,未必没有丁玲自我的反省,敏锐而富有热情的她一定在上海革命风潮的鼓动下,在胡也频积极投入的左翼运动中,感到了时代的变局所产生的激动人心之处,可能也因此反省自己早期的作品正流露着“没有出路的牢骚和悲哀”,而正因为这“没有出路”的景况是真实的,所以她必须寻求突围,她以美琳的选择来说明自己的思考:美琳原本的理想是拥有幸福的爱情,但在若泉和子彬的论辩中,她发现自己除了爱情之外一无所有,若泉在十字街头的忙碌和活跃与子彬在亭子间的骚乱和苦恼形成鲜明的对比,她无法再安于“五四”之后所拥有的幸福的家庭生活,而产生了参与社会同时也实现自我的美好愿望。在小说的结尾,一向被子彬认为是温柔娇美的美琳也走向了街头和群众。
相较于《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呈现丁玲思考女性如何自我实现的路径,在《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二)》中,丁玲则透过望微和玛丽难以妥协的冲突,更集中地思考“五四”个性解放与个人主义思想和20年代末期革命思潮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差异。望微希望能将生命的一切幸福,包括自我实现与爱情追求纳于革命理想之下,他期待与玛丽既是情人,又是同志,但玛丽向往“恋爱至上”的人生,主动追求全然的,完整的爱情,于是她最终选择离开望微。在丁玲笔下,玛丽早已摆脱莎菲在爱情中的犹豫不决、自怜自伤,是个自信美丽而积极主动的女人,但在对望微和玛丽的描写中,也未尝没有丁玲的判断。望微的革命信仰和他忙碌充实的实际工作让他的生命有了安顿之所,在他眼里,玛丽是个聪明美丽的女人,但她的出身和学识局限了她的思想:“她的聪明更造成她的骄傲,她的学识却固定了她的处世态度,一种极端享乐的玩世思想。她信仰自己,她不屈服人。有时她会更倔强更顽固起来。” 这字字句句都有丁玲深刻且坦率的自剖与自省的意味。当玛丽最终决定离开望微时,望微知道“他的信仰依然存在,他的思想不会为一个女人的去留而改变,他虽说在当时会很难过,然而他一定会用别一种力,他的理性来克服这残留着的爱情的弱点。”
这字字句句都有丁玲深刻且坦率的自剖与自省的意味。当玛丽最终决定离开望微时,望微知道“他的信仰依然存在,他的思想不会为一个女人的去留而改变,他虽说在当时会很难过,然而他一定会用别一种力,他的理性来克服这残留着的爱情的弱点。” 相较于望微的沉毅稳定,玛丽面对望微时则充满着爱情无法满足的焦虑和躁动,她因望微的忙于工作而感到生活的寂寞和沉闷,而望微的工作环境又让她产生格格不入的挫败感,她终于在争吵中对望微发出怒吼:
相较于望微的沉毅稳定,玛丽面对望微时则充满着爱情无法满足的焦虑和躁动,她因望微的忙于工作而感到生活的寂寞和沉闷,而望微的工作环境又让她产生格格不入的挫败感,她终于在争吵中对望微发出怒吼:
“我使你痛苦吗?笑话!是你在使我痛苦呢!你有什么痛苦?白天,你去 ‘工作’,你有许多同志!你有希望!你有目的!夜晚,你回到家来,你休息了,而且你有女人,你可以不得我的允许便同我接吻!而我呢,我什么都没有,成天游混,我有的是无聊!是寂寞!是失去了爱情后的悔恨!然而我忍受着,陪着你,为你的疲倦后的消遣。我没有说一句抱怨的话。现在,哼,你倒叹气了,还来怨我……”
玛丽对望微的不满其实正说明着爱情无法操之在我的非自主性。虽然玛丽果断地离开了望微,找到另一段幸福的爱情,但能保证她不会再次尝到“失去了爱情后的悔恨”吗?小说结尾虽然望微因示威抗议而被逮捕,但在他来说是“虽九死其犹未悔”,他看到玛丽被一个漂亮青年揽着,手里拿着许多包包,正耀眼而娉婷地从大百货商店门口走出。玛丽此时的形象尽管自信而快乐,但却呼应《阿毛姑娘》中现代城市文明的物质享受对女性的诱惑和吸引,如果阿毛姑娘的下场是抑郁苦闷,那么玛丽的生命会不会也遭遇同样的困境呢?
丁玲可以说是最早指出女性对现代物质文明,特别是流行服饰和生活享受的着迷的现代女作家,她在处女作《梦珂》中,就描写梦珂在姑母家见识到马车、洋房、客厅、沙发、地毡,又香又软的新床和天鹅绒的枕头,她对这些从未梦想过的物质享受感到迷醉。同样的概念在《阿毛姑娘》中有了更深刻完整的演绎。而到了《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二)》中,在望微坚定的信仰对照之下,玛丽的物质享受看似光鲜亮丽,却显得空虚无着,这对一直在思考女性生命处境和出路的丁玲来说绝对是个重要的提醒。许多丁玲传记、作品选集和研究论文集都会以毛泽东赠给丁玲的诗句“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来说明丁玲的转变,并且总是搭配着两张照片,前者是20年代丁玲在上海拍摄的,穿着绒毛洋装的,摩登女子眉眼略带忧郁的头像,后者则是丁玲1938年在西安拍摄的,身着军服长裤,带着微笑英姿潇洒的全身照,个人以为这之间的转变,《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之二)》的思考和选择正是关键。相较于《在黑暗中》文字和情绪的慷慨愤激或彷徨陷溺,《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之二)显得客观、理智,也明朗许多。正是通过真诚坦率的反省和冷静理性的思考,革命成为丁玲(女性)实现自我生命价值最重要选项之一,让文小姐走上“与革命相向而行” 的生命道路,也让女性自我实现的努力与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
的生命道路,也让女性自我实现的努力与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
革命绝非一条坦途,在此之后丁玲做了许多努力,例如她在1931年写作《一天》,丁玲透过大学生陆祥参与左翼运动的一天,描写知识分子如何对群众产生新的认识,并在艰困且充满挫折和不适应的革命工作中锻炼自我的意志,坚定革命的信仰,这其中必定有丁玲在实际革命运动中所获得的感悟,而在之后写作的《田家冲》和《水》中,她更将描写主体转移到她原本相对陌生的群众上。这些作品在文学表现上虽然尚未成熟,但却可以看到丁玲不断挑战自我的个性,挑战自我文学表现的习惯,也挑战自我看待社会问题与革命工作的看法。
也因为有这样的努力,丁玲才能在40年代初写出一系列包括《新的信念》《县长家庭》《入伍》《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夜》等优秀成熟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丁玲将曲折而复杂的革命过程中所遭遇到各种矛盾、冲突的问题尽纳于己,因此这些篇章几乎涵盖了个人、集体、启蒙、救亡、革命、知识分子、群众、理智、情感及新旧思想观念之间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可以说涵盖了“五四”以来最重要的社会与历史问题。而在参与革命也思考、书写革命问题的过程中,丁玲同时进行着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与自我改造。因此她在1950年5月所写的《〈陕北风光〉校后感》一文中,回顾了自己来到陕北之后的生命道路:
在陕北我曾经经历过很多的自我战斗的痛苦,我在这里开始认识自己,正视自己,纠正自己,改造自己。这种经历不是用简单的几句话可以说清楚的。我在这里又曾获得最大的愉快。我觉得我完全是从无知到有些明白,从一些感想性到稍稍有了些理论,从不稳到安定,从脆弱到刚强,从沉重到轻松……
但我总还是愿意用两条腿一步一步地走过来,走到真真能有点用处,真真是没有自己,也真真有些获得,获得些知识与真理。我能够到陕北,自然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当然也绝不是盲目的。
丁玲在写这篇文章的同时,可能也同时回顾了自“五四”启蒙之后所走过的崎岖的生命道路。在这条蜿蜒曲折又艰难的道路上,女性自我生命价值的实现可以说是让丁玲走向革命的强大动机,但高度的反省力、不怕苦的自我锻炼,以及为这个社会尽一份心力的热情才是使她终能走完革命全程的重要原因。也因此,她在《三八节有感》一文的最末给予女性同胞具体的“强己”办法,其精神包括:一、爱护自己,节制地生活,不让自己生病。二、靠着生活的战斗和进取,读书和做有意义的工作,让自己的精神愉快。三、用脑子、有理性,才能独立判断。四、要有为人类的大抱负,并且下吃苦的决心,坚持到底。 即使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依然是作为一个“人”很中肯也很艰难的生命锻炼。
即使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依然是作为一个“人”很中肯也很艰难的生命锻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