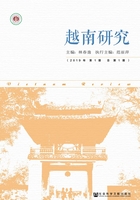
中越关系
中法战争前冯子材中越边境“清匪”的作用评析
唐凌[1]
摘要:19世纪7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争夺的重点逐渐转向亚洲,法国等列强觊觎越南和中国。越南此时内乱频发,农民起义和土匪暴乱交织在一起,严重危及越南的封建统治,也危及中国边境的安全。中越两国历史上形成的朝贡关系,决定了冯子材的“清剿”行动既要运用军事策略,也要遵守当时的外交原则。传统落后的中越交往体系制约了冯子材的手脚,持续不断的“匪患”动摇了中越两国封建统治的根基,触发了19世纪下半叶的边疆危机。
关键词:中越边境 冯子材 “清匪”
冯子材(1818~1903),广东钦州(今属广西)人,字南千,号翠亭,清末名将。综观其一生的活动,均与军事有关。其中,19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他受越南政府邀请和清政府派遣到越南平定当地起义军和哗变的清军,历史文献中,这一活动多被冠以“清匪”的名称。此活动历时长,所面临的局势复杂多变,不仅是对其军事能力的极大考验,也是对中越关系的一种重大考量。
这期间,正值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西方列强加强了对中国及其周边国家的侵略,中国开始出现严重的边疆危机。而中越边境,则成为危机的漩涡地带。这种形势,决定了冯子材的军事活动必然与边疆危机的应对密切相关。同时,反过来,也会对边疆危机的走向产生影响。因此,研究冯子材这个历史人物,必须以19世纪下半叶的边疆危机为基本背景。
冯子材在中越边境“清匪”的军事行动,《清实录》有较翔实的记载。《清实录》全称《大清历朝实录》,现通行的影印本4433卷,1220册,系清代官修编年体史料汇编。主要选录各时期上谕和奏疏。各朝实录记事细目多寡不均,但主要类别大多相同,举凡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及自然现象等众多方面的内容皆网罗包纳,是研究清代历史最基本的史料。以《清实录》的记载为依据分析冯子材的所作所为,前人已做了不少探索,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应该看到,过去有的研究所引用的资料是零碎的,有的甚至存在断章取义、张冠李戴的现象;有的虽然正确理解了文献的含义,不过由于就事论事,更由于缺乏系统的梳理与研究,对于边疆危机形势及其应对措施的认识,仍难以摆脱褊狭的局限。
针对这种状况,以详细解读《清实录》的文本为基础,对冯子材的“清匪”活动进行系统梳理,客观评析他在边疆危机应对中的作用,并对导致边疆危机的历史原因重新进行审视,进而对晚晴的外交政策进行反思,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毋庸讳言,《清实录》是清朝政治立场的集中体现,但是,由于当时越南等国仍与中国保持着朝贡关系,无论是政治、军事、文化还是经济方面,都对中国有着很强的依赖性,因此,当边疆危机出现时,与中国不能不采取相同的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说,《清实录》并不只是体现清朝的立场,越南等国的政治、军事取向,也往往包含其中。不仅如此,越南等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关系,也往往成为《清实录》记载的内容。显然,有关的信息对研究冯子材的活动同样能够提供间接的帮助。
一 冯子材中越边境“清匪”过程
通常认为,法国侵略越南的计划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开始实施,到70年代,步伐进一步加快,规模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越南内部危机也日益严重,持续不断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由中国逃入越南境内的天地会,更是加剧了越南社会的动荡。内忧外患的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使越南政府的统治陷入了困境,不得不请求清政府的援助。大致从这时起,《清实录》开始以较大的篇幅记载这方面的情况,直至越南被法国控制,越南与中国之间的朝贡关系破灭为止。据此,可将19世纪70年代作为考察的重点。冯子材是当时的广西提督,其地位决定了不可能参与战略决策,但是,他对中越边境危机的处置状况,却是中越当局决策很重要的依据。
从同治七年至光绪八年(1868~1882),冯子材主要受命在中越边境清剿由中国逃入越南的天地会吴亚忠部、越南的“叛匪”苏帼汉,以及清军在越南的叛将李扬才所部等。《清实录》的记载至少有51则,这些史料,多数为同治皇帝和光绪皇帝的“谕”,也有少部分当事官员的“奏”,从中透露出来的历史信息主要如下。
第一,清剿的军事布置由清朝廷直接确定,尤其是入境兵力的调动更是如此。负责清剿的冯子材等部,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当时,清政府对于中越边境的“清匪”态度较为坚定,因为意识到边疆不稳定,无论是对中国还是越南,都会带来很大的威胁。所以,面对频繁出现于边疆地区的“悍匪”或“叛匪”,不惜代价进行清剿。但是,越境清剿,则始终坚持限于边境地带的原则,同时,主要针对中越“匪徒”相互勾结的现象。例如:
同治七年十月二十日(1868.12.3):贼匪吴亚终(忠)等遁入越南境内,麇集谅平、木马、九葑等处,分股扰及太平边境……着苏凤文会商冯子材,督饬官军,会合夷兵,迅图进剿,务将此股贼匪悉数歼除,不得以贼去稍远,停兵不进,敷衍目前,致成不了之局。[2]
同治十年十月二十一日(1871.12.3):越南匪首苏帼汉等,虽声称投诚,仍复心怀反侧,自应乘其穷蹙,悉力歼除,以绝后患……其河杨(阳)、兴化等处,距边较远,自不宜穷兵深入,转至边圉空虚,该抚等当传知该国王自行攻剿。[3]
类似的记载,同治八年三月二十三日(1869.5.4)、同治十年二月二十五日(1871.4.14)、同治十年九月初六日(1871.10.19)的上谕中也均有所见。从这些记载中可知,对于越南境内的“悍匪”,无论是来自中国还是越南本地,清政府一方面派兵进行清剿,另一方面又要求冯子材等“不宜穷兵深入,转至边圉空虚”,以确保边境地区的安全稳定。冯子材在清政府的控制下用兵,行动无疑受到很大限制。而《清实录》的记载显示,他每次行动,都程度不同地取得成功,这说明其军事才能非同寻常。
第二,清剿过程中往往与越南相互配合,努力使行动合法化。“朝贡关系”之下,中国需要承担保护周边国家的义务。越南当时国力孱弱,更需要中国的帮助。面对各种“悍匪”的侵扰,其有限的兵力根本无力清剿,不得不请求中国派兵增援。冯子材作为广西提督,较为熟悉越南的地情军情民情,所以在越南“清匪”的过程中发挥较重要的作用。中越边境的“悍匪”,经常在中越两国来回运动,只要进入越南境内,冯子材根据清政府的指令,清剿行动展开时都注意与越方配合。例如:
同治七年六月十五日(1868.8.3):冯子材督帅部属追剿中越边界之吴亚忠余部,“并令太平府各属文武,将逐卜一路隘口严加扼守,以遏贼踪,一面札饬太平府知会越南夷官及各路文武员弁,会合剿灭”。[4]
同治十年二月二十五日(1871.4.14):着冯子材相度机宜,督同总兵刘玉成迅将木马一带股匪荡平,毋留余孽,并随时知照该国派兵会剿。[5]
同治十年五月初七日(1871.6.21):越南近又有股匪十数起,犹须慑以兵力。冯子材等拟俟各军到防后,约会该国,先将边界各匪分别剿抚,即分军扼要驻扎,随时相机应援。[6]
总兵李扬才率部入越剿匪,后因滋事被朝廷革职查办,于是起兵反叛朝廷,冯子材奉命对其进行围剿。
光绪五年五月十二日(1879.7.1):逆首李扬才各股份踞者岩等处,虽经冯子材督率官军,将左舍、板道以致滩头先后攻克……惟地方辽阔,贼垒至九十余座之多,亟应认真剿洗。冯子材现已行至北圻,着即严督各军赶紧进剿,毋再迟延干咎。并知照越南派兵分扎防堵,以杜窜越。[7]
光绪五年九月初九日(1879.10.23):现据越南官禀报……逆仍在太原等省辖境山谷藏匿,冯子材已招募该国山人五百名配入各营,分投(头)引兵搜捕。[8]
这几次行动,清政府要么“知会越南夷官及各路文武员弁,会合剿灭”,要么“知照该国派兵会剿”,要么“约会该国,先将边界各匪分别剿抚,即分军扼要驻扎,随时相机应援”,要么“招募该国山人”协助清剿,总之,根据越南清剿形势选择不同的合作方式。清政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对世界的形势有所了解,开始接受国家之间的交往原则与方法。同时,越法《第一次西贡条约》签订后,法国觊觎越南的野心及其活动也引起了清政府的警觉。所以在平定中越边境“匪患”的过程中,尽量争取越南的合作与支持。冯子材作为军事行动的执行者,对清政府的这些谕令深刻领会,贯彻坚决,既积极进剿,又利用越南的力量组织攻防,所以,每次行动,尽管遇到许多阻力,但由于有越南政府和军队的参与,大都能有效克服,逐渐清除“匪患”。
第三,在越南“清匪”的同时,加强中国边境的防卫。这一方面是取决于“匪情”的变化,另一方面则是取决于当时中越关系的变化以及中越边境地区严峻的形势。《清实录》中,各种谕令反映出清王朝对当时中越边境的局势十分担忧,例如:
同治十年十月初七日(1871.11.19):粤西今年以来,吏治军政,废弛已极……至该省兵力,半驻越南边境,内地本不免空虚,着冯子材迅将邓建新等股匪及早歼除,以绥藩服,并可腾出兵力,会商刘长佑择要布置,绥靖强圉。[9]
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1874.1.2):越南国边地被匪窜扰,前经谕令冯子材督饬官军,出关剿办。嗣以兵勇不宜久驻外国,且虑有骚扰情事,是以叠准刘长佑等所奏,将各营陆续撤回。兹据该国具疏吁请,朕腃顾藩封,殊深轸念。此时粤西官军,如另出境剿匪,究于该国有无裨益,且不至别滋事端之处。着刘长佑、冯子材悉心妥筹,迅速具奏,并着礼部传令该国王知悉。[10]
光绪五年三月初二日(1879.3.24):冯子材亲赴太原剿贼……该省边防紧要,杨重雅、冯子材务当严饬各营实力防范,毋任匪踪扰及内地。[11]
中国封建社会实行中央集权制,边疆地区由于远离政治中心,统治力量一直相对缺乏。近代以前,中越边境地区一直未进行有效开发,社会发展基础因此非常薄弱。同治皇帝和光绪皇帝之所以对中越边境地区的防卫空虚十分担忧,正是因为看到了这种状况,尤其是了解到广西“吏治军政,废弛已极”,而兵力“半驻越南边境”后,更是顾虑重重,所以下令“着冯子材迅将邓建新等股匪及早歼除,以绥藩服”,“可腾出兵力,会商刘长佑择要布置,绥靖强圉”。不久,鉴于越南国王再次请求出兵帮助“清匪”,明确提出“粤西官军,如另出境剿匪,究于该国有无裨益,且不至别滋事端之处”,必须“着刘长佑、冯子材悉心妥筹”方可做出决定。而且,必须确保“毋任匪踪扰及内地”。
第四,越南政府在清剿过程中显得较为被动,不仅助长“匪焰”,而且增加了中国军队的负担。《清实录》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很多,有些表述较为含蓄,有的则较为直白,坦陈具体事实,尤其是局势严峻、军事压力大的情况下,更是不回避困难,不遮掩失望与抱怨,例如:
同治十年正月初十日(1871.2.28):此次越南夷匪苏帼汉、刘泳(永)幅(福)、邓志雄等,向在该国垦田授职,俱非吴亚终(忠)之党,现因越南夷官办理失宜,致令群起为难。[12]
同治十年七月初一日(1871.8.16):匪徒如此猖獗,越南何以毫无布置,任其奔窜?着即知照该国严密堵御,毋令该匪阑入腹地。冯子材尤当严饬出关将士及留防兵丁,不可稍有扰累,并随时与该国官吏联络声势,庶彼此情意相洽,方易奏功。[13]
同治十一年七月初八日(1872.8.11):刘玉成等所部兵勇,现因越南尚未派兵接防,一时不能入关。冯子材已照该国所请,暂留镇、柳、选、建等营,遏扎太辖,现筹选练防军,慎固封守。[14]
行政处置失当、防守缺位或迟缓等,都是越南政府被动的反映。正因为如此,越南的“匪患”禁而不绝,剿而复起,造成社会持续动荡。清政府对此十分不满,却又无可奈何。
《清实录》关于冯子材在越南“清匪”过程的记载较为翔实,这说明,当时越南内患确实非常严重,清剿十余年而未断绝,不仅危及越南政权,而且给中国的边境安全带来严重隐患。这同时说明,当时的清剿局面很复杂,除涉及军事力量的调动和军事行动的策略外,还涉及外交关系的处理,所以,当事官员不断奏报,清政府才不断发出谕令。上述活动,冯子材作为前线军事指挥几乎全都参与,并且取得突出“战功”,显示出他在近代中越关系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二 冯子材中越边境“清匪”的作用
判断冯子材中越边境“清匪”的作用,仅凭上述记载是不够的,还需要进行统计分析和比较分析,因为当时与他同时承担着相同任务的,还有其他清朝官员。只有通过统计及比较分析,才能更为接近历史的真相。
如前所述,从同治七年至光绪八年(1868~1882),是冯子材奉命在中越边境开展“清匪”军事行动的时间。同治十一年(1872)前,剿灭的对象主要是天地会余部吴亚忠及越南叛匪苏帼汉等。《清实录》记载的史实至少共有24则,其中,以冯子材名义上奏的有2则,以刘长佑和冯子材两人名义上奏的有2则;同治皇帝专给冯子材的谕令有15则,给苏凤文和冯子材共同发的谕令有5则,这些奏折和谕令,均围绕中越边境地区的“清匪”问题而形成。刘长佑和苏凤文都曾任广西巡抚,属清朝的封疆大吏,在清剿中越边境“匪患”中肩负重要职责,但是,真正率军进行清剿的,则主要是广西提督冯子材。可以说,在中越边境的安宁及中越关系的处置上,冯子材的作为至关重要。《清实录》尽管没有进行具体评析,但其所记录的事实,已对这种重要性予以明确肯定。从光绪元年至八年(1875~1882),《清实录》记载冯子材等在中越边境“清匪”的史实共有27则,其中,以光绪皇帝名义专发给冯子材的谕令有22则,给广西巡抚杨重雅等和冯子材共同发的谕令有5则。事实上,清剿李扬才的军事行动主要在光绪四年至五年(1878~1879)进行,因此绝大多数的谕令主要在这两年发布。此后的一些谕令,其实只是对冯子材的嘉奖而已。深入研究这些谕令,不难看出,与同治时期的“清匪”情况相比,此时冯子材及其所部面临的形势更严峻,清剿的难度也更大,所以谕令的发布更频繁更具体。最初,谕令多为催促,后来,逐渐改为战略部署与战略合作的要求,最后则是清剿结束后遗留问题的处理。《清实录》虽然重在记载清帝关于中越边境“清匪”谕令的内容,以战局的分析和中越两国军事行动的指示为核心,但是,通过对比谕令内容前后的变化,就可以看到冯子材取得了令清朝廷满意的战果。
作为前线军事指挥官,冯子材为“清匪”可谓不遗余力。许多行动亲自督战,奋力克敌。如同治八年八月初七日(1869.9.12),“土匪勾引逆首吴亚忠,分踞木马、高平,意欲并力死守”。冯子材“督带兵勇分路进攻”,“先后将马腹隘等处贼垒平毁……克复高平夷省”。[15]清叛将李扬才系中国职官,“带领匪徒扰及藩服,致令该国清兵援救”,光绪皇帝认为是朝廷的耻辱,[16]下令痛剿,以维护国体。冯子材深知责任重大,“亲率各军次第攻剿”。[17]李扬才人多势众,分踞深山老林,凭借天险予以顽抗,更重要的是,他们是真正的亡命之徒,绝不会束手就擒。冯子材率军每攻克一处巢穴,都要真正做到知己知彼,有勇有谋,攻守进退,万无一失。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冯子材及其所部与其周旋,最终将其擒获,押送回国斩首示众,为中越两国清除了一大隐患。对于溃散的“悍匪”,冯子材“督将弁实力搜捕,以期各境土匪尽数铲尽,毋致异日重烦兵力”。[18]另外,为瓦解“悍匪”力量,减少损失,他还将收降人员“尽数带回内地……分起遣送回籍”,[19]从而为“清剿”创造了另一种有利的条件。冯子材所清剿的“匪”,有的是中越农民起义军,有的是两国的叛将,属性完全不同,但是,对中越两国统治者而言,凡是危及自己统治的反抗行为,均为“匪患”,必清除之而后快。冯子材对清政府忠心耿耿,执行“清匪”任务决心坚定,行动迅速果敢,战果辉煌。在当时入越清军将领中,他的表现异常出类拔萃。据《清实录》记载,与冯子材同时入越承担“清剿”任务的其余将领,要么未被赋予实权,要么因不适应地情难有作为,要么因失职而被查办。如上思州刘琢,于李扬才拥众出关,未能设法拦阻,被视为疏于防范,“着交部议处”。[20]道员赵沃贻误军情,尽管曾取得不少清剿战绩,也被革职。[21]而冯子材在各种清剿活动中多能张弛有度,应对自如,克敌制胜,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十余年的时间里,牢牢掌握中越边境的“清匪”大权。作为驻守边关的汉军将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特例。
清朝廷对冯子材的信任,反映在许多方面,如同治十年六月二十日,皇帝将刘长佑调补广西巡抚后,于次日降旨,指出越南边境“时有匪徒滋扰,叛服靡常,若非封疆大吏振刷精神,极力整顿,不足以绥靖边圉”。特别强调“冯子材现在带兵剿办越南窜匪,刘长佑当与和衷共济,以期迅速蒇功”。[22]道员覃元琎因病交卸兵事,同治皇帝下令交由冯子材处置,并要求“所有太(平)、镇(安)军情,该提督均当妥筹兼顾”。[23]光绪帝从中越边境多年的“清匪”形势中,也看到了冯子材非凡的军事才干,面对此起彼伏的“匪患”和严重的边疆危机,明确指出:“该提督系专阃大员,呼应较灵,是以派令前往。”[24]“冯子材自督师出关以来,叠次进剿。将贼巢全行荡平,甚属奋勉出力。”[25]
朝贡关系下,在中越边境“清匪”,经常带兵入越境打仗,势必要与越南军队及政府进行交涉。清政府赋予冯子材很大权力,如同治十年五月初七日(1871.6.24),越南“悍匪”苏帼汉就抚后,仍复观望怀疑,加上“近又有股匪十数起,犹须慑以兵力”,皇帝指示“冯子材等俟各军到防后,约会该国,先将边界各匪分别剿抚,即分军扼要,随时相机应援”。[26]毫无疑问,“约会该国”,等于承认冯子材可以代表中国政府与越南直接进行“清匪”事务的交涉。同年七月初一日,根据越南“败匪窜扰”的形势,同治皇帝在谕令中提出:“冯子材尤当严饬出关将士及留防兵丁,不可稍有扰累,并随时与该国官吏联络声势。”[27]这同样意味着清王朝不仅充分信任其军事才能,而且信任其政治才能。光绪五年八月十一日,鉴于叛将李扬才及其所部藏匿深山老林,行踪难觅,清王朝下令“迅咨越南国王,饬地方官确查李逆等实在下落”。尽管此令同时下达给刘坤一、张树声和冯子材等人,但是,冯子材作为军事指挥官,也能获得向越南国王咨询的权力,显示出其独特而重要的政治地位。
在中越边境“清匪”过程中,冯子材多次受到清朝廷的嘉奖,例如,同治九年闰十月十六日(1870.12.8),在已“赏给骑都尉世职”的基础上,“着加恩再赏一云骑都尉世职,以示优奖”。[28]光绪五年,因剿灭李扬才有功,被保举“优叙”。[29]
当然也要看到,刘长佑、苏凤文、杨重雅等封疆大吏均与冯子材共同参与中越边境的“清匪”行动,他们在各自的奏报中,共同肯定冯子材的军事才能,支持冯子材的军事行动。这也是同治皇帝和光绪皇帝对其信任,使其能连续建功立业的重要原因。
三 冯子材“清匪”与19世纪下半叶的边疆危机
冯子材中越边境“清匪”的行动,与19世纪中后期中国边疆危机究竟存在何种关联?这是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众所周知,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与周边不少国家的外交关系,都建立在“朝贡关系”的基础上。1883~1885年,中法两国因越南问题而引发的战争,不仅使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也最终促使中国与周边国家朝贡关系的崩溃,刺激了列强侵华的野心,导致边疆危机的出现。
而法国之所以敢于在发动中法战争前侵略越南,正是利用了越南国内统治虚弱的时机,同时也利用了清政府面对列强侵略,既担心引火烧身,又害怕越南局势失控,危及边境安宁,影响自己统治的矛盾心理。
法国主教百多禄1787年(清乾隆五十二年)向国王路易十六提出奏议,[30]帮助法国确立了“伟大的法兰西东方帝国”计划,随之,法国开始了侵略越南,进而侵略中国的行动。1872年,法国商人堵布益在政府的授意下,企图以武力通过红河,被越南政府阻止。次年,法国将深入中国长江上游的安邺召回,令其率军攻打河内。从此,越南与中国面临严峻的战争形势。冯子材中越边境“清匪”行动,势必对当时的中越及中法关系产生影响。
中越两国长期形成的朝贡关系,使清政府不得不承担保护越南安全的义务。清廷虽然对西方列强殖民扩张的意图已看得比较清楚,但是,对于究竟如何应对却始终很茫然。对于这种陈旧的朝贡关系的弊端与所带来的风险,更是缺乏清醒的判断。同治七年(1868),当接到越南国王咨文,请求派兵协剿吴亚忠及越南叛匪时,皇帝立刻下达清剿的谕令:“该国久列藩封,恭顺有加,乃任内地匪党扰及边隅,何以副朝廷怀柔远人之意?归顺、凭祥等处既有踞匪,兵力不能兼顾,即着苏凤文、冯子材等,添募劲旅,分道并进,越境疾攻,会同越南夷兵两面夹击,迅歼丑类,以靖边疆。”[31]
法国准备攻打河内之前,清政府认识到越南的局势将会更加复杂,自己必须做出筹划,于是要求在越官员调查有关情况:“安南陆路,接壤广西,由广西边界至胥江道里若干?有无山川阻隔?着苏凤文密派干练有识之员,前往该处确访一切情形,绘图贴说,并将近日安南与法国情意是否融洽之处,据实奏闻。”[32]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清政府对越南的国情其实非常缺乏了解。面对日益严重的“匪情”,以及越南政府反复提出的援助请求,清政府从稳定大局出发,仍然同意派兵支援,但是,如前所述,严格限制在中越边境,而且用兵之后尽快撤回。安邺率军攻打河内后不久,同治皇帝在谕令中明确指出:“越南今日情形益加贫弱,黎裔等患近在国中,滨海地方又为法国蚕食,其势岌岌,几难自存。该国不能自强,动招外辱,在中国抚绥藩服,自难恝然。第越境用兵,可暂而不可久。”[33]清廷没有料到,法国出兵越南,只是为了夺取一个侵略中国的跳板,其最终的目的,是扩大战争,全面吞并越南,继而占领中国,实现其“伟大的法兰西东方帝国”计划。随着法国侵略越南步骤的推进,清政府发现局势越来越难以掌控,自己的统治面临越来越大的危机,因此,焦虑与犹豫交织在一起,使应对之策暴露出明显的矛盾状态。“越南各匪,在宣光、河南一带,分股掳掠,据报法国带兵攻破越南河内省城,官多被掳,兵有伤亡……现在越南夷官踵营求救,自应相机防剿,以顾外藩。……粤军于边关内外堵剿越南各匪,与法兵绝不相涉。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行照会法国使臣转饬遵照,毋令别滋事端。”[34]光绪皇帝执政后,主张对列强采取强硬对策,同时,改变派兵入越“清匪”,疲于应对,动摇本国根基的状况。指出:“该国伏莽甚众,防不胜防,断无以中国兵力代为剿捕之理……即传知该国王自行攻剿,严清余孽。”[35]但是,由于他并未真正掌握实权,这些主张实际上并未能得到有效贯彻落实。清政府仍然按照慈禧及奕 、李鸿章等封建顽固派和投降派确立的政治方针,延续历史上形成的“朝贡关系”,继续派兵支持越南“清匪”,同时,极力避免与法国发生正面冲突,以确保中越两国政府的统治得以维持。
、李鸿章等封建顽固派和投降派确立的政治方针,延续历史上形成的“朝贡关系”,继续派兵支持越南“清匪”,同时,极力避免与法国发生正面冲突,以确保中越两国政府的统治得以维持。
将清政府19世纪70年代在中越边疆“清匪”问题上所持的态度做一梳理,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协助越南政府“清匪”是其一贯的方针。1873年安邺率法军进攻河内,内外交困的局势迫使越南当局加紧向清政府求援,而清政府的胆怯刺激了法军的侵略野心,也助长了“悍匪”的嚣张气焰。再将《清实录》关于冯子材中越边境“清匪”的51则记载做一梳理,可以看出,责成他奋力剿匪的谕令约占35%,要求他在越南境内用兵之后即刻回撤的约占28%,加强边境防守的约占30%,要求他避免与法国军队接触,或者不在法军所经之地“清匪”的约占7%。清政府的这种态度,决定了冯子材很难有所作为。而事实上,冯子材具有突出的军事才干,在中越边境“清匪”过程中,几乎每战必胜。《清实录》记载冯子材的“剿匪”情况,尽管会出现一些催促甚至埋怨的语言,但是,了解了每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再联系相关因素分析,就不得不承认,冯子材的所作所为大都得到政府的认可,也得到越南政府的支持及赞赏。无论是越南的“悍匪”还是中国的叛将,都视冯子材为克星,避之唯恐不及。“清匪”十余年而未能断绝,并非冯子材智谋不足,军事不力,实则由清政府软弱的对敌方针所致。其对外妥协、对内限制剿匪行动的措施,设置了极大的障碍,束缚了冯子材及其所部的手脚,诱发了中越两国的社会矛盾,催生了边疆危机。
18世纪下半叶,越南内乱迭起。阮福映在法国主教百多禄帮助下夺取了政权,后来被清王朝册封为越南国王。他的这种经历,对中越、中法、越法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时的越南王朝十分虚弱,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朝贡关系,使其在政治的天平中,不得不暂时倾向清王朝,尤其是在国内“匪患”频起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清实录》记载阮朝向中国求援的史实共有约20则,可以这样说,无论是入境的吴亚忠部,还是本国的农民起义军,或是“叛匪”,越南阮氏政权都无力“清剿”,必须依靠清政府的帮助。而清政府将“清剿”的范围限于中越边境,又使各种“匪情”剿而不绝,延续不断。为争取清王朝的支持,阮氏政权有时还要向入境“剿匪”的清军支付一定的“犒师银”。[36]越南兵勇参与“剿匪”,也需大量粮饷,但库存十分有限,不敢轻易动用。冯子材等奏报“越南应领米价脚费,自应归款”,越南国王咨称“不敢具领”。后来同治皇帝亲自下令,“将前寄北库银三万八千余两,仍截存夷库,以示体恤”,[37]以打消其顾虑。长期“清匪”,同样耗费了清政府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增加了巨大的负担。光绪帝公开表示反对继续支持越南“清匪”,实际上也是迫于这种负担过于沉重。越南阮氏政权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继续寻求清政府帮助的同时,于1874年与法国签订《法越和平同盟条约》和《法越商约》,力图通过向法国开放市场,赢得其支持,缓解社会矛盾,减轻统治压力。结果却是加剧了法国的侵略,促使其占据越南北部,强迫开放红河后,卷土重来,再次以武力占领河内。将《清实录》中冯子材“清匪”过程中与越南当局交涉的记载做一分析,就可以发现,尽管清政府要求“夷兵”积极协助,但是,真正发挥作用的均为入境“清匪”的清军,尤其是冯子材所统率之部。阮氏王朝的统治虚弱,造成其军队非常缺乏战斗力,以至于当时越南的贡使在“匪患”频发的情况下无法正常行动,需要冯子材派兵护送。大象是当时越南的贡品之一,理应受到精心保护,却被“悍匪”抢夺,后被冯子材部夺回,才使这一贡品免受损失。接着,越南贡使准备送京进呈,同治皇帝担心远道跋涉,惊扰沿途各地,下令冯子材将贡象“发给夷官领还,毋庸解京”。[38]在越南国内发生这种现象,足以说明其当局已经很难确保社会稳定。
以上所述,就是冯子材在中越边境“清匪”所面临的形势。概括起来,19世纪后半叶,资本主义争夺市场的重点开始转向亚洲各国,越南和中国成为法国觊觎的重要目标。中越边境长达十余年的“匪患”,给法国实施侵略创造了有利条件。冯子材的“清剿”,帮助越南和清政府消除了许多隐患,但是,越南政府的虚弱和中国政府的胆怯,使“匪患”清而不绝,更使法国的侵略野心膨胀,最终促使其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这似乎是一个历史的悖论:冯子材在中越边境“清匪”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边疆危机的局势没有得到缓解,却愈发严重。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清政府和越南政府的腐朽无能,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1885年,冯子材领导中国军民取得镇南关大捷,而清政府却与法国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历史的悖论再次演绎,令人可叹、可悲、可恨!
研究中法战争前冯子材中越边境“清匪”的作用,目的不仅仅是对这个历史人物做出客观的评价,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对这段历史的回顾,探索中越关系发展演变的进程,同时,找到19世纪下半叶中国边疆危机产生的根源。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以史为鉴,在国际交往中看清方向,寻找正确的合作方式。
The Role of Feng Zicai in Bandit Suppression along the Sino-Vietnamese Frontier before the Sino-French War
Tang Ling
Abstract:Since the 1870s,Asia became a main arena for colonial competition. Western powers such as France pretended to Vietnam and China. Meanwhile,Vietnam was in chaos. Peasant uprising and riot interwove together,becoming a serious threat to the stability of Vietnam,as well as to the security of China’s frontier. Because of the long-lasting tribut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Vietnam,Feng Zicai had to adopt a dual strategy to suppress the bandits. On one hand,he had to use military strategy,on the other hand,he had also to follow diplomatic principles. This traditional pattern of Sino-Vietnamese relations restricted Feng Zicai’s action. The problem of bandit undermined the rule both in China and Vietnam,resulted in a crisis on the frontier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Keywords:Sino-Vietnamese Frontier;Feng Zicai;Bandit Suppression
Đánh giá phân tích vai trò của Phùng Tử Tài trong cuộc chiến chống thổ phỉ biên giới Trung-Việt trước cuộc chiến tranh Trung-Pháp
Đường Lăng
Trích yếu:Trong những năm 70 của thế kỷ 19,trọng điểm cuộc cạnh tranh giữa các nước tư bản chủ nghĩa trên thế giới dần dần chuyển sang Châu Á,Pháp và các nước mạnh bắt đầu nhòm ngó Việt Nam và Trung Quốc. Lúc này,nội bộ của Việt Nam thường xuyên rối loạn,cuộc khởi nghĩa nông dân và bạo loạn thổ phỉ cùng lúc diễn ra,gây nguy hiểm nghiêm trọng đến sự thống trị của nền phong kiến Việt Nam và nguy hiểm đến an ninh biên giới Trung Quốc. “Hệ thống triều cống” được hình thành trong lịch sử hai nước Trung Việt đã quyết định rằng hành động “tiêu diệt bọn thổ phỉ” của Phùng Tử Tài đòi hỏi vừa phải vận dụng cả chiến lược quân sự,vừa phải tuân thủ các nguyên tắc ngoại giao ở thời điểm đó. Quan hệ truyền thống lạc hậu giữa Trung-Việt đã hạn chế hành động và kế hoạch của Phùng Tử Tài,tiếp đó “nạn trộm cướp” không ngừng làm lay động nền móng thống trị phong kiến của hai nước Trung-Việt,gây ra cuộc khủng hoàng biên cương cuối thế kỷ 19.
Từ khóa:Biên giới Trung Việt;Phùng Tử Tài;“Tiêu diệt thổ phỉ”
[1] 唐凌,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
[2] 《清实录·穆宗实录》卷245,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3] 《清实录·穆宗实录》卷322,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4] 《清实录·穆宗实录》卷235,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5] 《清实录·穆宗实录》卷306,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6] 《清实录·穆宗实录》卷310,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7] 《清实录·德宗实录》卷94,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8] 《清实录·德宗实录》卷100,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9] 《清实录·穆宗实录》卷321,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10] 《清实录·穆宗实录》卷356,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11] 《清实录·德宗实录》卷89,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12] 《清实录·穆宗实录》卷302,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13] 《清实录·穆宗实录》卷315,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14] 《清实录·穆宗实录》卷338,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15] 《清实录·穆宗实录》卷264,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16] 《清实录·德宗实录》卷83,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17] 《清实录·德宗实录》卷97,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18] 《清实录·穆宗实录》卷273,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19] 《清实录·穆宗实录》卷272,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20] 《清实录·德宗实录》卷85,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21] 《清实录·德宗实录》卷91,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22] 《清实录·穆宗实录》卷314,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23] 《清实录·穆宗实录》卷240,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24] 《清实录·德宗实录》卷82,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25] 《清实录·德宗实录》卷99,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26] 《清实录·穆宗实录》卷310,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27] 《清实录·穆宗实录》卷315,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28] 《清实录·穆宗实录》卷295,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29] 《清实录·德宗实录》卷102,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30] 张雁琛译《1787年百多禄主教上路易十六奏议》,《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1),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第363~364页。
[31] 《清实录·穆宗实录》卷245,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32] 《清实录·穆宗实录》卷287,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33] 《清实录·穆宗实录》卷350,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34] 《清实录·穆宗实录》卷359,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35] 《清实录·德宗实录》卷97,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36] 同治九年(1870),经冯子材督军越剿,将吴亚忠首要各逆“悉数歼除”,“越南国王馈送犒师银两,该提督婉为辞却”。见《清实录·穆宗实录》卷295,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37] 《清实录·穆宗实录》卷303,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38] 《清实录·穆宗实录》卷322,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