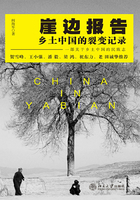
族群
崖边最早叫吴家崖边,因为来崖边最早定居的人姓吴。但吴家人在崖边发展了100年以后绝迹了。后来崖边成了厉氏的“天下”。厉氏家族人丁兴旺、发展迅猛,在晚清出了一个武举人,成了真正的原住民,至今已在崖边生存近200年,繁衍了9代人。厉氏家族习惯将崖边称作厉家崖边。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兵荒马乱,崖边迎来了更多的人家,崖边遂变成了各个家族互融共存的多族群村庄,崖边的称谓始终没能冠上厉姓。
封建时代政权、神权、族权(夫权)统治农村,其中的族权就是宗族概念。在江西湖南一带,宗族观念尤其浓厚。有的宗族还有自己的武装,护卫着村寨。湖南大庸西教乡熊氏家族的武装力量强大,贺龙率领红军于1928年8月攻打时花费了七天时间。 在崖边没有如此强大的宗族,整个陇中地区也没有。这与陇中地区交通相对便捷,地域人群迁移频繁、混居杂聚有直接关系。
在崖边没有如此强大的宗族,整个陇中地区也没有。这与陇中地区交通相对便捷,地域人群迁移频繁、混居杂聚有直接关系。
崖边所在的通渭县是“千堡之乡”,县境内现存堡寨1000余处,县境内有记载的最久远堡寨为北宋时期修筑。离崖边最近的岳家山堡子大约建于明朝时期。堡寨是通渭地区古代重要的军事防御设施,明、清、民国各时期,官方、民间都在修筑堡子。 众多的古堡证明通渭地域信息通达、战乱频临、人口流动频繁,难以形成聚村而居的宗族,所以通渭农村只有一些较大的家族。
众多的古堡证明通渭地域信息通达、战乱频临、人口流动频繁,难以形成聚村而居的宗族,所以通渭农村只有一些较大的家族。
土地革命时期,崖边的地主就出自厉氏家族。除了厉姓家族之外,崖边较大的家族就是我的阎姓家族,至今已有百年历史。宋、孙、王、佟、谢、许等家族都来村时间较短,至今人丁不旺,势力不大。
一个村庄居住着几大家族,也就形成了几大势力。家族是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组成的重要部分,家族的强弱、大小直接关系到整个族内人群的生存发展、社会威望、社会地位。整个崖边的历史中,族群冲突和家族之间的斗争贯穿始终。尤以阎厉两个家族的斗争最为激烈,影响最为广泛。
厉氏作为崖边的原住民,对所有外来户都充满了排斥。这和今天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市民排挤外来人口如出一辙。
厉氏家族的人从来不把另姓人放在眼里,经常声言崖边是厉家的崖边。但厉氏家族人在外来户面前趾高气扬的威严逐渐被阎氏家族打破了。
我的太祖父刚来崖边时一无所有,他在村庄的最高处择崖壁挖出一口洞穴,将自己的生命安顿了下来。他居住在洞穴中,既要抵御深夜的寒风,又要防御凶狠的狼群。他的夜晚异常孤独,多少次梦境,他都被呼啸的西北风和突然传来的狼叫声惊醒。夜晚无疑是一种煎熬。白天,他会用一捆柴草堵上自己的洞穴,步行20公里路,去榜罗镇一个叫“万兴隆”的商铺站柜台。
厉氏有个被称作厉家老爷的人,是睥倪一世之人。我太祖父在厉家老爷的屋舍旁耕地时,给耕牛衔着一对巨大的铃铛,来回耕地一天,那铃声深沉、持久地震慑一天。厉家老爷对此非常反感,但一忍再忍,没有咒骂。这种情况要换成别人,注定要被厉家老爷痛斥。
厉家老爷的猪四处糟蹋庄稼,忽一日,他家的猪来到我爷爷家里祸害,被我爷爷痛打并追到了厉家老爷的家门口,然后得理不饶人一顿斥责。厉家老爷面对斥责一时慌了手脚,理亏之际却也哑口无言,我爷爷胜利班师。
第二日,厉家老爷便向村里人发泄不满:“那姓阎的,凶得厉害”。
从此,厉氏家族对阎氏家族说话做事也掂量着来了,不像过去根本不放在眼里。
梳理崖边的家族斗争史,这个事件,恰恰是阎氏一个外来户扎根崖边的标志。支撑一个家族在村中崛起的基础是经济,太祖父离世时,已在崖边置办土地100亩,修建房屋一大院。
解放前,我的爷爷阎兴堂由于思想激进,热衷于政治活动。为了防止自己的孩子被国民党抓壮丁,他参与过国民党的保安团。后来他加入中共地下党。解放前夕,他和其他地下党员将国民党保安团的枪支弹药悄悄埋于地下,配合当地和平解放。解放后,他参与了当地的政权工作。我爷爷的革命经历让我的家族具有政治上的先天道德优势。而厉氏家族家业庞大,阎厉矛盾在所难免。
厉氏家族按照排行,共有七房人。其中年龄最小的厉世荣继承了祖上的家业,其他兄长都分家另住,因而田产多、有雇工的厉世荣被评定为地主。产生了地主的崖边厉氏家族对新政权的不满,相当于就是对外来户阎氏的不满,因为阎氏从头到尾参与着政权政治工作,他们将对干部的不满也上升为对政权的不满。
厉氏人中,直到1960年,还有人对共产党有蔑称。不触及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就很难读懂中国近当代史,也很难理解“地富反坏右”这个词组的来历。有了对底层现实社会问题的认识,就更容易读懂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
厉奉月性格倔强,他对厉氏家族被新政权评定为地主一直怀恨在心,故而终身反党。随后发生的一件事让阎厉两个家族结下了世仇。
阎作林是我三爷的儿子,据说当年阎作林在为生产队种谷子,他偷藏了一点谷籽,准备回家吃,但被厉奉月发现了。厉奉月说:“三喜(阎作林乳名),宁可吃屎,也不能吃籽。”还将阎作林揪到我爷爷跟前论理。在这件事情上,显然是阎作林有错,而厉奉月抓住了阎氏家族有人犯错的证据咄咄逼人,将成年积聚的仇恨用阎作林藏谷籽事件作为了爆发口。两人激烈争吵。
我爷爷阎兴堂和我三爷不和睦,斗争了半辈子。但我爷爷对阎作林这个侄子还是多有偏袒。厉奉月常年观点偏右,而我的爷爷观点偏左,那年月政治形势总体偏左。为了赢得争吵的胜利,我爷爷最后以厉奉月常年反党为由将其举报到了人民公社。厉奉月被人民公社以“反革命罪”送到了县上,关押期间,遗憾地意外身亡。从此,阎氏和厉氏结下了巨大的仇恨。好在新的社会关系造成了家族的解体,厉氏家族的人对阎氏家族的人有仇恨,但他们自身也不团结,自己内部难以团结往往难以克敌。阎厉矛盾便一直没有爆发出来。
我的三叔阎武曾担任过崖边生产队会计,他回忆说:“厉奉月是刀子嘴豆腐心。作为同村人,将厉奉月举报给公社是我爷爷一辈子所犯最大的错,有公报私仇的嫌疑。尽管他死于意外,但起因和我爷爷有关。”
不过我的家族中其他人一律不认为我爷爷有错,党员干部就应该维护党组织的荣誉,这是政治伦理,党的干部举报反党行为理所当然,这是党章、党纪明文规定的。
宋氏是崖边另姓人中较大的家族。宋氏一族人和厉氏、阎氏都有一些矛盾。阎氏和宋氏本来没有什么纠葛,但宋守忠和老婆佟氏离婚后,佟氏又和我三叔阎武成婚,引燃了阎氏和宋氏两个家族之间的仇恨。
困难时期,宋守忠的父亲为生产队上交公粮的过程中,死在了半路。据同行人讲,宋守忠的父亲由于长期饥饿,担粮的过程中,一次性吃掉了一天的干粮——荞面锅盔,是胀死的。其时全村人都陷入饥饿,上公粮这种公差需要重体力,故而才有了一顿能吃饱的荞面锅盔。但宋守忠的父亲长时间饥饿忍不住一口气吃完了一天的干粮,暴食葬送了一条鲜活的生命。当时,我的爷爷阎兴堂是石湾公社山庄生产大队的副书记,直接分管着崖边生产队的工作。宋氏一门人便诬告是我爷爷阎兴堂害死了宋守忠的父亲,前后写了28份诉状。宋氏一族人认为和阎氏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尽管仇恨的种子从此埋下,不断发酵,但一直没有爆发大的冲突。
阎氏由于我爷爷阎兴堂在解放后担任了生产队的干部职务,得罪了很多人。后来,我三叔阎武担任了崖边生产队的会计,我的大伯阎林当兵分配到天水地区工作,1950年代末期因说了老家饿死人的真实情况,在“反右倾运动”中被发配原籍,也来到了石湾公社。在崖边人看来,阎氏一族产生了“三级”(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干部,这引发了很多人对于阎氏家族的嫉恨。
1958年至1960年,通渭县爆发饥荒,崖边未能幸免。1960年上级政府派来了工作组,督查基层工作,特别是饥荒事件。1961年,我爷爷阎兴堂、大伯阎林、三叔阎武全部被关押起来,进行审查。我奶奶晚年回忆说:“父子三人全部关起来了,把人吓死了,我给你爷爷做了一双新布鞋,等死着了。心想着这一次父子三个肯定要法办,肯定是死定了。”
我爷爷、大伯、三叔三人被关在一起,由民兵把守,不准见家人。他们一面接受工作组的审查,一面还要接受全村社员的批斗。我家族中人回忆说,当时全村人都在积极检举我爷爷等人的问题。厉氏家族举报我爷爷陷害了厉奉月;宋氏家族举报我爷爷害死了宋守忠父亲、检举我三叔抢走了宋守忠的老婆;就连和我爷爷一起搭班子的生产队干部也检举我爷爷的人格道德有问题,说我爷爷是“糜面嘴,豆腐心”,意思是嘴甜,但人心不可靠。全村人将各类问题一股脑倾倒出来,目的就是要将阎氏家族的三名干部统统法办。
但工作组将阎氏三人关押了15天,批斗了15天之后,出人意料地放了。原因是崖边人所反映问题没有一件能够落实清楚。饥荒事件是全国刮“五风”导致粮食过多上缴出现的结果,非小小的生产队干部所为;厉奉月意外死亡在通渭县,非阎兴堂迫害致死,阎兴堂检举他发表反党言论并无过错;宋守忠父亲死亡的真正原因是由于长期饥饿,暴食荞面锅盔引发的;阎武抢走宋守忠老婆的事情更是无中生有,因为佟氏乐于和我三叔过日子,属于自由婚姻;至于生产队干部反映的问题只能当做民主生活会同事之间为了促进工作开展的批评发言。
1961年,阎氏父子三人尽管没有被法办,但阎兴堂和阎武都被革职,阎林回城工作。1964年,我爷爷阎兴堂因病去世。同年,阎武再次复出,担任了崖边生产队会计,直到改革开放初期。2004年至今,我的大哥阎海平又担任了崖边行政村主任职务。阎氏从解放以来,基本上一直有人担任村里的干部职务。
随着时代的发展,族群之间的裂痕和明争暗斗依然存在着。过去的仇恨在时间的推进中隐形延续,但毕竟时代已经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化,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交往、交流变得更加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各种社会交往更加频繁,封闭环境下形成的族群矛盾已很难再掀起大的波澜。因为每个族群自身也早已分化、破裂。大家的利益诉求变得更加多元,很难再形成几大家族或派系的勾结互斗,所有的斗争基本以户与户的局部矛盾细碎化、单一化而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