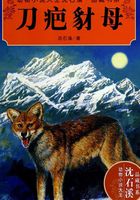
第5章 刀疤豺母(5)
其他豺也跟着这几只失子的雌豺咆哮起来,真正是群情激昂,同仇敌忾啊。
我担心刀疤豺母会顶不住这种压力,向豺群发出攻击我们的指令。它虽然是这群豺的首领,恐怕也不能完全不理睬众豺的意愿。果然,它眼角上挑,鲜红的舌头来回磨动白森森的犬牙,似乎产生了扑咬之意。我赶紧学着豺的样子,将嘴唇往上翘,吊着嗓子左声左气地说:“你千万别干蠢事,今天你要是伤害了强巴,我发誓,明天我就会带着狩猎队来把你们通通消灭的。冤冤相报何时了啊!你若肯放我们一码,我保证,一定设法把你们丢失的八只幼豺还给你们……”
它肯定听不懂人类的语言,但它似乎从我诚实的表情和庄严的语调中领会到了某种东西,上挑的眼角又放平下来,嘴巴也重新闭拢。
歪嘴巴雌豺狂啸一声,不顾一切地蹿上来,欲咬强巴。刀疤豺母纵身一跃扑过去,一头撞在歪嘴巴雌豺的腰上,把它撞开去。
呦——刀疤豺母冲着在地上翻滚的歪嘴巴雌豺吼了一嗓子,那是在严正警告:没有我的同意,谁也不准胡来,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歪嘴巴雌豺爬起来,抖抖身上的草屑泥沙,呦呦呜呜不停地叫唤起来。我虽然听不懂豺的语言,但从它愤怒的表情和委屈的声调中不难猜测它是在向众豺倾诉自己的小宝贝被掳走的悲痛心情,控诉刀疤豺母在袒护仇敌。
好几只豺朝刀疤豺母投去不满和疑惑的眼光,有两只母豺噼噼啪啪狠狠地甩打自己的尾巴,以发泄心中的怨气,有两只公豺不怀好意地绕到刀疤豺母背后,摆开扑咬的架势。
也许是报仇心切,也许是觉得众豺都在支持自己,歪嘴巴雌豺变得有恃无恐,再一次像股疾风似的蹿上来,张嘴要咬强巴的后脖颈。刀疤豺母怒啸一声,迎面拦截,举起一只爪子朝歪嘴巴雌豺的脸上撕抓,歪嘴巴雌豺扭头躲闪,刀疤豺母以闪电般的速度一口将歪嘴巴雌豺的右耳朵咬了下来。
歪嘴巴雌豺半只脑袋血淋淋的,惨嚎一声,落荒奔逃。
刀疤豺母威风凛凛地仰天长啸,那只耳朵还在它的犬齿间弹跳,嘴吻涂抹着一层殷红的血浆。
众豺都被震慑住了,那两只心怀不满的母豺识相地停止甩打尾巴,那两只不怀好意的公豺知趣地收敛起扑咬的架势,顺从地蹲伏下来。
也许,在桀骜不驯野性十足的豺群社会里,只有采用最严厉的惩罚手段,才能保住首领的权威。
刀疤豺母重新面对着我和强巴,伫立着,静穆了好几分钟。它的眼神中没有敌意,也没有仇恨,只有深深的无奈和无尽的悲苦。终于,它叹息般地轻啸一声,扭头朝坡顶走去。
豺群也都乖乖地跟着它撤离了。
我目送着豺群远去,暮色苍茫,刀疤豺母走得很慢,脊梁弯塌,脑袋勾垂,尾巴拖地,一副身心交瘁的模样。
九
当天夜晚,我们回到野外观察营地后,洗了个澡,换了衣衫,强巴便开始自斟自饮喝闷酒,把一瓶习水大曲全喝了下去,喝得酩酊大醉,便开始说醉话,一会儿说要去金沙江淘金,赚了钱买一百条凶猛的藏獒,专门训练它们对付豺狗,要把天底下所有的恶豺一只不剩地通通消灭光,一会儿说要去买一挺机关枪来,再遇到豺群,嘟嘟嘟嘟横扫过去,把它们全部扫倒……
翌日中午,他才从醉梦中醒来,闷着头抽了一锅烟,扛起那只装着八只幼豺的柳条筐,便朝山里走去。我问他要到哪里去,要去干什么?他也不搭理我,只顾往前走。
来到那棵歪脖子小树下,他放下柳条筐,抬头朝那条悬吊在树枝上的豺尾瞄了一眼。那是断尾公豺的尾巴,已经挂了半个月。他抽出腰刀,跳起来一刀砍断绳索,象征着复仇的豺尾掉了下来。然后,他又打开柳条筐,将八只幼豺放了出来。
获得自由的幼豺们,呦呦咿咿地叫着,在树下奔跑嬉闹。
强巴拉着我,往山顶一片杂树丛跑去。
我们刚躲进杂树丛,便听到山沟传来豺嘈杂的啸叫声,我用望远镜看去,嚯,我所熟悉的那群金背豺,不知从哪个旮旯里钻了出来,聚集在那棵歪脖子小树下。好几只母豺将自己失散多日的小宝贝搂进怀里,一遍又一遍深情地舔吻。幼豺们在母豺的膝下钻进绕出撒欢撒娇。一派母子团聚的动人景象。
我慢慢移动望远镜,寻找刀疤豺母。哦,它蹲在一块圆形石头旁,守着面前的一只幼豺。这只幼豺并没因为回到豺群而高兴,蜷着身体缩在落叶里,样子很忧伤。刀疤豺母伸出舌头去舔吻它,它竟然扭头躲开了。刀疤豺母抬起伤感的脸,望着天空出神。
就在这时,山岬传来一声豺啸,一团红色的影子飞也似的从山沟蹿出来,转眼间来到歪脖子小树下。我仔细看去,哦,是昨日被刀疤豺母咬掉右耳朵的歪嘴巴雌豺。它在树下东张西望,焦急地寻找。刀疤豺母看见歪嘴巴雌豺了,眉眼宽慰地舒展开,呦呦叫了两声,退到一边去。歪嘴巴雌豺急忙蹿到圆形石头旁,一见到那只蜷缩在落叶里的幼豺,激动得连叫声都变了,呦呜呦呜,不知道是悲还是喜,一下子跳过去,把那只幼豺严严实实罩在自己的身体底下,拼命地舔,拼命地亲,呕出一些糊状物来,嘴对嘴地渡食给幼豺。那只幼豺也变得活泼起来,在歪嘴巴雌豺腿上亲昵地摩蹭啃咬。
哦,这只蜷缩在落叶下的幼豺,原来是歪嘴巴雌豺的亲骨肉。
过了一会儿,歪嘴巴雌豺总算平静下来,带着那只幼豺来到刀疤豺母面前,用一种羞愧的表情,替刀疤豺母整饰背毛,好像在为自己昨日的唐突与冒犯请求原谅。刀疤豺母则小心地舔了舔歪嘴巴雌豺缺损的右耳朵,好像在为自己昨日过于严厉的惩罚手段深表歉意。
好几只母豺也都拥到刀疤豺母身边,有的舔吻它的脖子,有的梳理它足踵间的毛丛,有的依偎在它身上,看得出来,它们都很钦佩它敬重它。
豺群要走了,当其他豺簇拥着八只幼豺快要拐出山沟时,刀疤豺母站在歪脖子小树下,面朝着山顶的杂树丛,长啸了三声,然后才撒腿奔跑去追赶它的豺群。我想,它一定知道我和强巴藏在杂树丛里,它是在用豺的特殊方式向我们致谢哩。
就在这时,强巴突然掏出插在腰带上的牛角号,腮帮鼓得像只皮球,呜呜吹响。随着牛角号阴郁低沉的声调在空中散播开,在我们身后约百米远的一道石坎里,呼啦冒出一排人头来,有的戴着毡帽,有的扎着头巾,有的缠着兽皮,一看就知道是在山林里滚爬摸打的猎手。强巴唰地举起了猎枪,就像发出了某种事先约定的指令,站在石沟里的那排猎手齐刷刷地举起了长筒猎枪。我大吃一惊,很明显,强巴背着我暗中组织卡扎寨的猎手,埋伏在那道石坎里,个个手执猎枪,是不是想利用豺群解救和接回那八只幼豺之际将这群金背豺一网打尽?这也太卑鄙太阴谋太恩将仇报了呀!我不敢冒充英雄用胸膛去堵那排黑森森的枪口,为保护金背豺去堵枪口算不上是一种明智之举。我只能有气无力地喊出一个字:“不——”
没人听我的,强巴甚至连看也不看我一眼,便扣动了扳机。砰!清脆的枪声在我耳边响起,紧接着,身后石沟里响起一排枪声,震耳欲聋的枪声在山谷回响,空气中弥漫开一股刺鼻的硝烟味,呛得我连连咳嗽。完了,我想,这群金背豺完蛋了。豺群还没有拐出山沟,还在猎手们的视野和长筒猎枪的有效射击范围之内,二三十支猎枪齐射,就像镰刀割麦穗那样,起码死伤百分之九十以上。我机械地站起来,朝豺群望去,奇怪的是,它们并没有像被镰刀割断的麦穗那样纷纷倒下去,仍好端端地站在哪儿,瞪着惊诧的眼睛,扭头朝身后张望。我当然不相信金背豺有刀枪不入金刚不坏之身,我也不相信那帮闯荡山林的猎手突然间个个都变成近视眼或斜视眼。我如坠云里雾里,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时,刀疤豺母呦地发出一声长长的哀啸,那是奔逃藏匿的命令。霎时间,公豺和母豺分成若干个小群体,簇拥着自家宝贝幼豺,四散逃窜,有的钻进茂密的灌木丛,有的蹿出山沟外。砰!砰砰!站在我身边的强巴又扣响了猎枪,石坎里的猎手们也跟着打出了第二排霰弹。我这才看清,强巴和所有猎手的枪口都指向天空,霰弹打在树梢上,纷纷扬扬洒了一场翠绿的叶子雨。
“你这是干什么呀?”我迷惑不解地问。
“我要用枪声告诉这些豺,我们不欢迎它们,我们讨厌它们,我们希望它们从尕玛尔草原搬走,从这块土地上消失!”强巴脖子上青筋暴突,牙巴骨咬得嘎喳嘎喳响,斩钉截铁地说。
“这群豺帮了我们大忙,要不是刀疤豺母出手相救,我俩早就被驴蹄踩得粉身碎骨了,你却……”我伤心得说不下去了。
“要不是看在这点情分上,我早就送它们到阎王爷那儿报到去了。”强巴说,“它们救过我一次,我也饶了它们一命,谁也不欠谁了。豺是恶兽,是灾星,是魔鬼,必须将它们撵走。”
我懂了,虽然这群金背豺在关键时刻帮了我们大忙,虽然刀疤豺母竭尽全力阻止狂怒的豺扑咬强巴,可并没有使强巴彻底改变对豺的恶感与偏见。强巴是条血性汉子,信奉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的处世原则,这群金背豺救过他,他记住这份情义,所以抬高枪口朝天开枪,放这群金背豺一条生路。但在强巴的心底里,金背豺曾虐杀他爱犬雪娇的仇恨并未泯灭,牧民对豺的成见丝毫也未减弱,所以会开枪威逼这群金背豺离开尕玛尔草原。
传统势力非常顽固,惯性思维十分害人。
金背豺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强巴和那帮猎手仍乒乒乓乓朝天开枪。那是在用武力威胁恫吓,传递人类对豺不友好的态度。
“要是这群金背豺拒绝迁徙他乡,继续留在尕玛尔草原,你们要怎么样呢?”我忧心忡忡地问。
“我已经不欠它们的了,我们是先礼后兵。”强巴遥望高黎贡山白皑皑的雪峰,一字一顿地说,“要是它们还赖在这儿不走,为了尕玛尔草原的和平与安宁,我们将组织一支狩猎队,无情地消灭这些恶豺!”
我忍不住打了个寒噤,为这群金背豺未来的命运而担忧,心里忐忑不安,也不晓得如何才能消弭当地牧民与金背豺之间无谓的仇恨。
“它们毕竟帮过我们,尤其是刀疤豺母,表现得还不算太坏。”强巴大概瞧出了我的心思,附在我耳畔轻声说道,“我也不愿意用我的猎枪瞄准刀疤豺母的胸膛。可尕玛尔草原只要有恶豺在,牛羊就会遭殃,牧民就过不上太平日子。即使天神下凡,也洗刷不尽恶豺的坏名声。我们牧民和豺是水火不能相容的。”
我沉默不语。我只能用沉默来表示抗议。
“你不用太为它们担心,”强巴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这些豺脑袋瓜灵得很,它们会揣摩人的心思,知道我们朝天放枪的用意,也许今天晚上就会离开尕玛尔草原到别处去谋生的。”
但愿如此,这是避免当地牧民与金背豺发生流血冲突最好的办法了。我暗暗祈祷。
那天晚上,我借宿在卡扎寨强巴家的毡房里,躺在暖融融的氆氇床垫上,身体感觉很疲倦,脑子却格外清醒,老想着刀疤豺母和它率领的那群金背豺,为人类强加在它们身上的坏名声深感不平,为当地牧民对豺的误解和偏见深感遗憾,为它们今后的命运深感忧虑,胡思乱想辗转难眠。凌晨两点,鸡叫头遍,睡意这才姗姗来迟。闭起眼睛迷迷糊糊刚要入睡,突然,寨子里的狗集体吠叫起来,就好像在过狗的狂欢节一样,它们噼里啪啦奔跑,扑通跳跃,汪汪汪汪乱叫。睡意像露水似的蒸发了,我睁开眼,猜测寨子里的狗为何如此兴奋吵闹。过了一会儿,黑夜里亮起松脂火把,寨子里响起人的脚步声和呐喊声。我听见有人在毡房外大声喧哗:“快来看哟,恶豺搬家喽!”我急忙从氆氇床垫上翻爬起来,掀开厚厚的牦牛皮门帘,冲出门去。
月亮像只大银盘,高高地悬挂在蓝莹莹的天空上,明亮的月光将大地照得如同白昼。寨子正对面就是高黎贡山的日曲卡雪峰,一条薄云像银腰带缠扎在山腰上。峰顶终年不化的积雪在月亮下银光四射,闪耀着璀璨的光华。全寨子男女老少都出来了,翘首向日曲卡雪峰方向张望。我也举目望去,在一条通往雪山垭口的山脊线上,有几十个黑影,正在缓慢移动。白雪映衬,月光照耀,能见度极高,虽然隔着宽阔的山谷,黑色的剪影清晰可见,尖尖的嘴吻,蓬松的尾巴,粗短的四肢,圆圆的耳郭,尤其是背部那条厚密的毛带,泛动着碎金似的光亮,一看就知道是一群金背豺在行走。
“恶豺搬家喽!牛羊平安喽!”
汪汪汪——汪汪汪——
人在欢呼,狗在吠叫,寨子热闹得就像在开庆祝会。
白雪覆盖的山脊线,正在缓慢移动的金背豺黑色的剪影突然停了下来,走在队伍最前列的那只豺扭转脑袋,抻直脖子,朝着卡扎寨和山脚下那片绿意葱茏生机盎然的尕玛尔草原啸叫起来。我虽然看不清带头啸叫的那只豺的模样,但我可以肯定,它就是刀疤豺母。随着刀疤豺母做出啸叫姿势,所有的豺也都摆出引颈高吭的姿态来。
呦(左口右欧)……呦……(左口右欧)……呦呦……(左口右欧)(左口右欧)……
雪山垭口吹来的寒风,将豺的啸叫声传播得很远很远。
豺的嗓子本来就喑哑粗俗,啸叫声聒噪难听。群豺嚎月,音调长短不一,就像群鬼在哭泣,悲凉、凄惨、哀戚,听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豺们啸叫个不停,发泄心中的愤懑。